宅家久了就会随机获得一种“怪人”气质?丨新书预告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雷戈尔。他某日早晨醒来,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甲虫。
躺在安静的卧室内,这只甲虫多少有些不自在,它率先想到的是再睡一会儿,来忘掉这“一切愚蠢无聊的事”。尝试无果后,睡眠问题又让它联想起了工作上的烦心事种种——害,操劳过度总是让人显得有些悲哀。
似乎只要房门尚未打开,房间内发生的一切怪事都可以被允许。这是卡夫卡关于房门的一个隐喻,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一种表达。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现代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分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以正常人的面目示人;而在私人生活中,只要不被发现,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因为这种分界,每个人都被迫接受一个割裂且难以分辨的自我:面向他人时,我们必须伪装;面对自己时,我们害怕曝光。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最终蜕变为监狱,我在每个角落都撞见自己。”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如今,距离卡夫卡的时代已有一个世纪。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愈发膨胀,每天依旧是24个小时,但每一秒似乎都要被填满;社会与私人的分界依旧存在,但我们的注意与精力却被它们肆意地抢夺着。得益于网络的普及,我们既可以在工作时处理私人事务,又可以在家里处理工作,我们习得了“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的能力,也习得了迅速“切换”自己状态的能力。
唯一不变的是这样一种钟摆的状态:工作和社交让我们更加倦怠与过劳,渴望逃回自己的空间;而消遣和娱乐却又让我们更感孤独和空虚,渴望从自我中逃离。
“生活始终是一种在门槛上的存在。”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我们似乎被卡在了生活的两端,被生活拒之门外。于是困顿与绝望,让我们愈发退缩,让我们逐渐变得冷漠、无动于衷,让我们想要无限期地推延生活来临的时刻。可是如同格雷戈尔的处境,“房门”最终也没有成为他的屏障,而是变成了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刃——此时,它落下或不落下来,又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因无所作为而精疲力竭,承受着一种伪装成平静的隐性暴力。”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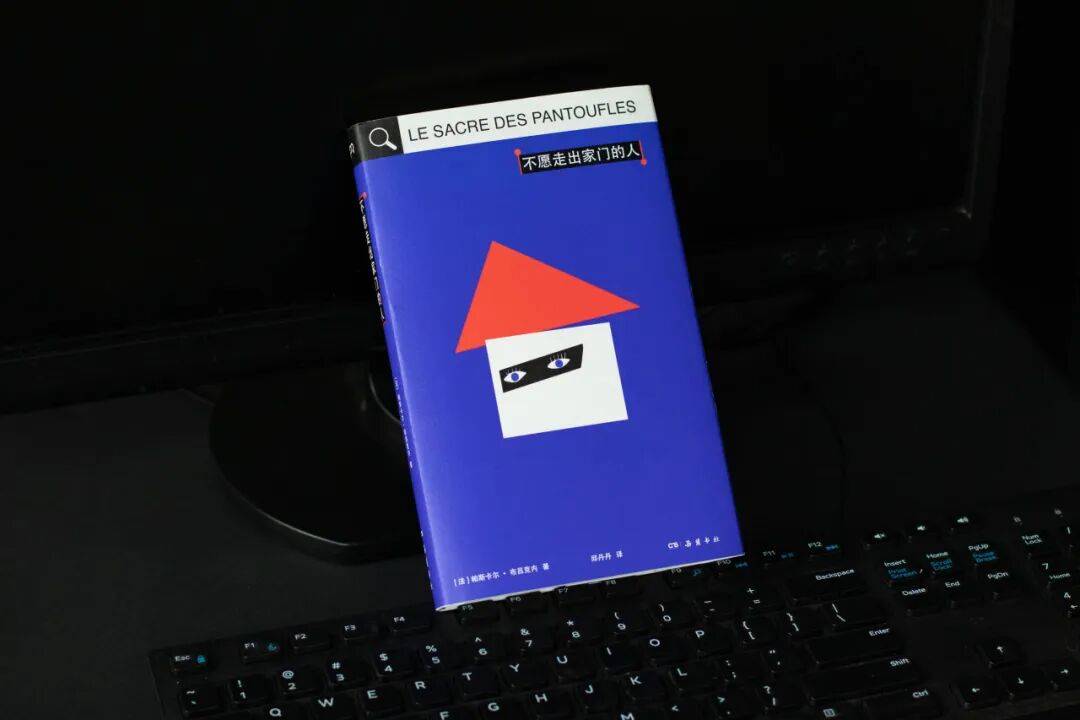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是的,一个人宅家久了,就会获得一种“怪人”的气质。因为他面对的,如同布洛赫所说,是一个“在我们内部燃烧的世界”。
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通病,这个时代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不愿走出家门的“怪人”。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尔维尔到普鲁斯特、卡夫卡,从尼采、萨特到齐奥朗、列维纳斯……这种不愿走出家门的“退缩”和“躺平”精神贯穿文学、心理学和哲学。那些一反常态、不愿再前进的“怪人”不仅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也是他们在生活中的形象。
沿着这条线索,当代知名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创作出了《不愿走出家门的人》。这本备受全球媒体赞誉的沉思录,梳理了我们这个时代背面的精神危机和现代人的心灵隐疾。他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写出我们生活中那些挣扎不得的心态,以及那些深不可测的细节。
以下文段选自《不愿走出家门的人》的第十二章。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你理解并喜欢自己随机获得的那种不太合群,也不合时宜的“怪人”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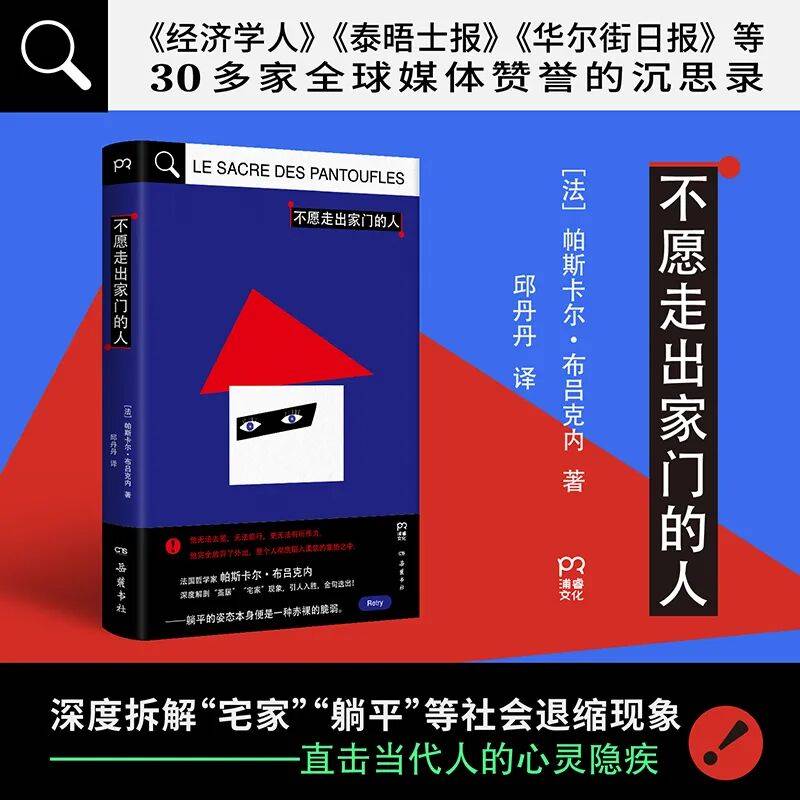
12
现代性的逃逸者
面对困扰我们的种种弊病,我们怎能不追思19世纪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学思潮?它既针砭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又质疑精英的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似乎被撕裂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埋头工作、积敛财富,服膺于理性计算的冷酷逻辑;另一方是反抗者,他们分裂为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者与反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革命者。他们唾弃庸俗的资产阶级及其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在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抗议声此起彼伏,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家与年轻画家的叛逆之言不绝于耳。然而,在这场对峙中,一个屈指可数的第三阵营悄然浮现——生活的逃逸者。他们既不反抗,也不工作。他们拒绝自己的时代,选择 对存在发起罢工,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这一立场。即便浪漫主义自1830年起逐渐左倾,试图洗刷其被指责为资本主义遮羞布的恶名,这些逃逸者依旧无意加入任何阵营。他们既拒绝资产阶级,也拒绝反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躺平的人生与夭折的人生共享同一条轨迹。这群革命风暴中的逆子不愿为未来播撒种子,而是希望未来成为一片贫瘠的荒原。他们既不创立学说,也不追随学派,而是将这条思想暗线潜藏在过去两百年的诸多作品之中——从德·梅斯特到佩雷克,以及其间闪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贝克特和卡夫卡(尽管这些作家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思潮)。他们唯一的激情是扼杀激情,唯一的欲望是压抑欲望。即便是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平庸,在他们眼中仍显得过于喧嚣躁动。这些平民渴望的是一种绝对的宁静。无须宣言、不用纲领,仅凭一股冷却一切的意志,便足以成为治愈现代世界癫狂的最佳解毒剂。这些平庸的追随者信奉无为的真理,推崇静止的伟大,执着于米歇尔·维勒贝克口中“低空飞行的存在”。

在法国文学中,最先赞颂室内生活的作家,非泽维尔·德·梅斯特莫属。1795 年,他写下了《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这是一部与以往那些描写冒险远行与英雄征服的叙事背道而驰的作品。德·梅斯特因与一名皮埃蒙特军官决斗而被软禁于都灵,正是在这段幽禁时光中,他创作了本书。德·梅斯特堪称“反卢梭”式的人物:卢梭是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云游者,曾徒步穿越过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而德·梅斯特则被法庭判罚,被迫在一间仅有一名仆从的豪华房间中度过漫长的禁足期。作者用42章细致地描述了这间房间的种种魅力所在:从睡榻到衣柜,从爱犬罗西娜到仆人乔内蒂,从书籍林立的书架到墙上精致的铜版画。这间房间,最终成了书中的真正主角,它不仅是作者沉思的空间,更是激发灵感与遐想的精神舞台。维克多·雨果在《一个死囚的末日》中便借鉴了这一叙述手法。这场“静止之旅”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创伤的一种回应。正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的那群青年男女,为逃离1348年肆虐佛罗伦萨的黑死病选择隐居乡间。德·梅斯特同样讴歌了这种能够保护人们免受世间丑恶的避世状态。深陷幽禁之中的他意识到,即便生活再困苦,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人们仍能凭借阅读、遐想与梦境,摆脱痛苦,超越苦难,而不会因此感到屈辱或低人一等。原地旅行有其独特的优势,无须花费分毫,不必承担风险,穷人可享,胆怯者适宜,懒惰者尤爱。“起来吧,怠惰之民!”来场无须远游的旅行吧!这种“室内想象力”引导人们从床榻到单人沙发,再从单人沙发到玄关,强调的不是直线前行的高效,而是曲径通幽的自在。这种体验看似单调却不乏妙趣。“温暖的炉火、几本书、几支笔,便足以抵御无聊。而当我们放下书和笔,专注于拨弄炉火,任思绪翩跹,沉浸于温柔的冥想,或随性编撰几句诗行来取悦友人时,那更是无尽的愉悦!时光便在这样的静谧中悄然滑落,无声地坠入永恒,而我们却丝毫不曾察觉其悲伤的流逝。”在温暖舒适的床榻上,作者展开翩然想象,踏上一场通往最奇幻世界的精神之旅。阅读德·梅斯特的作品时,仿佛在翻阅2020年那一年中层出不穷的“隔离日记”。房间成了无数潜在旅行的起点—尽管这些旅行从未真正发生过。德·梅斯特为仆人与爱犬的忠诚潸然泪下;当他凝视那位优雅的公爵夫人肖像时,灵魂便能“瞬间跨越千万里的距离”。他与著名学者及古希腊哲人(如柏拉图)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部作品看似自嘲幽默,叙述中亦不时自我解构,然而,这场旅行却在无声中催生了人造的狂喜和虚妄的惊叹,在对封闭生活颂扬的背后,潜藏着对逃离的深切怀念。德·梅斯特以轻盈笔触掩饰内心的苦涩,并从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中汲取灵感,由此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自我探索的文学潮流。这部充满讽刺与智慧的作品,后来被无数次模仿,甚至在1798年还出现了一部名为《我口袋中的旅行》的作品。

每本书都配备三张“宅人”书签
【新书推荐】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作者: [法]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出品方: 浦睿文化
原作名: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译者: 邱丹丹
出版年: 2025-11
家,已不仅仅是容身之所,更是一个逐渐令外出变得多余的全功能茧房。倦怠与过劳、社交恐惧、普遍孤独、浪漫主义的萎缩……让越来越多的人避居家中。而无论从工作到娱乐,还是从社交到消费,所有的生活必需都可经由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得到满足。在这部充满洞见的作品中,哲学家布吕克勾勒出一幅“足不出户便可安度余生”的社会图景,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哲学等多维度探讨了“宅家”“茧居”等社交退缩现象,引经据典,金句迭出,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