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读画家事
潮新闻客户端 王源

候雨不至,反而是朋友圈淘的两部书到手。均涉及画史或画家个案研究。
一本是王犁先生所著《喧嚣与孤寂——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札记》,书不太厚,但方法很新,王犁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郭麒麟,都有少年老成的特色,郭用舞台相声的功底去演电视剧,再用电视剧的节奏与角度去改造小品;同样,王犁细分专业是国画人物题材的博士,他大约是通过群像式的塑造,给研究课题赋予某种清晰的时代场景与人物形态,也如同浙派人物画的笔墨,将写实性与概括性组合,部分置换了写意性,从而使文章的可靠性和观点的可持久性得以大幅提升,我相信当他以同样的写作精力再返回到绘画创作,有可能搞出更高明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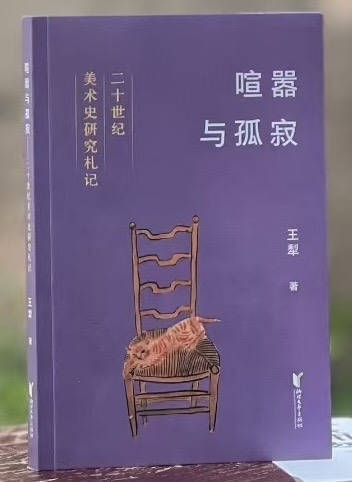
《喧嚣与孤寂-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札记》王犁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
《札记》中论题不拘大小,均可见学人底色,比如篇幅占比最大的浙派人物画专论,开篇“谈浙派人物画研究”,几乎囊括了浙派人物画的代表艺术家、与这一流派关系紧密的教师与领导、其他系科美术史论研究者的观点及文献提要,而第二篇“浙派人物画缘起和影响”,则将视角拓展至浙派人物画形成期的外部环境,比如其他专业院校对浙派人物画的态度,以及浙派人物画风格对非浙派的人物画家的影响,这两篇文字,不仅是较为完整地建立了浙派人物画相关的公共文本索引,而且对这一流派形成期间遭遇的中西绘画、京杭学院等流派或机构之间的资源竞争与观念碰撞,王犁都能要言不烦地记录在案,并稍加点评,使得他的个人文本拥有良好的叙事性而非情节性的张力。
尤为值得单独拿出来说说的是“1960-1966的林风眠与傅雷——《傅雷家书全编》钩沉”一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位均在法国留学过的艺术与翻译界的翘楚,通过艺术品的海外交易产生密切交集,这反映了王犁对特殊甚至稀有选题的敏感度与把握能力,以及相应史料的考证调度,这也得益于他与众多学者、画家、名人后代保持着良好的联系与交谊,方能从小题目中做出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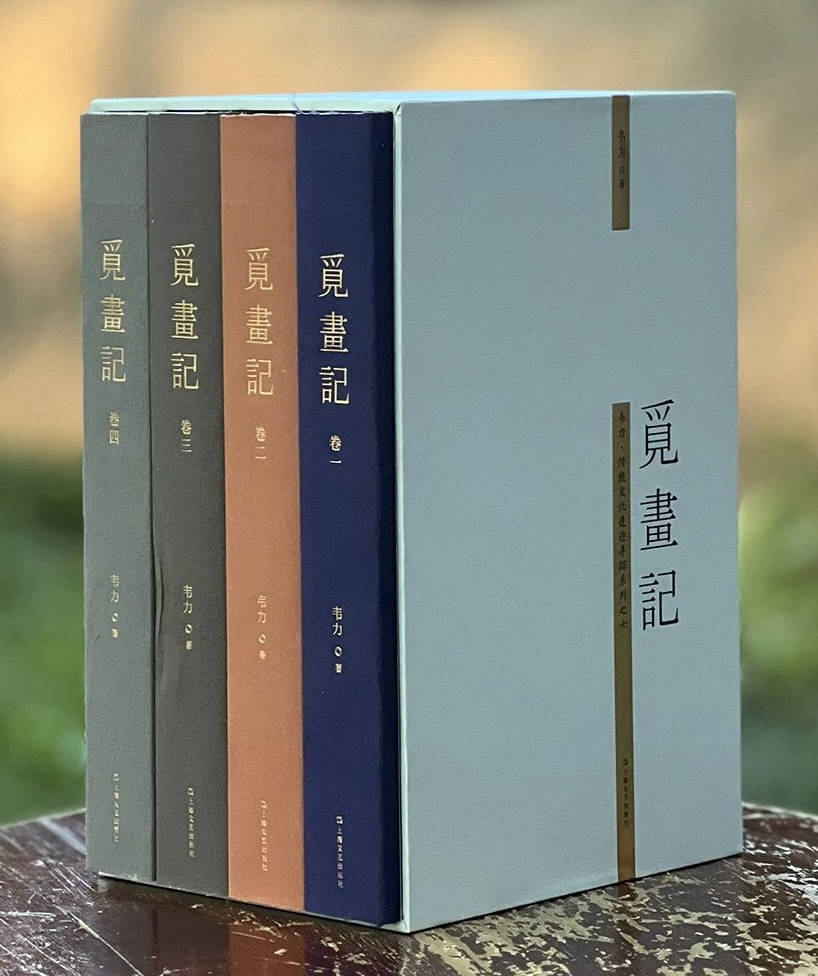
《觅画记》(全四卷)韦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第一版。
另一套是韦力先生所著《觅画记——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之七》,四厚本,韦力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藏书家,他的特点是善于跑现场,有点像刑侦学里的痕迹检查专业人员,他写的每一位画家,即便是南朝顾恺之,初唐阎立本,有条件的话,都会去其纪念馆、墓地仔细勘查,通过现场唤醒记忆,将史料的时间碎片进行空间拼接、重组,从而获得一种可感、可信的直觉输出。
同样是写林风眠,王犁着重写距今60年前,林风眠与傅雷在上海的交往,而韦力则以2013年1月雪后造访杭州灵隐路上林风眠故居一事作结,两位作者的文笔叠加,仿佛为读者打开了上帝视角,在阅读王犁引而不发的叙述时生成的某种愁绪,竟然在韦力的不平则鸣中抒发出来,让我对两本书的互文性更觉感佩。
这又让我想起了沈语冰先生前几天转发的在复旦大学艺术哲学专业创建五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他提到从黑格尔到丹纳,抑或海德格尔或贡布里希,对具体作品个案的研究都不太多,这是国际艺术哲学的一个短板,当然,他也列举了有几位法国学者相对注重作品研究,大约他主导的复旦艺术哲学系,也正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沈先生的观点,当然涉及到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进化问题,比如社会学、风格学、图像学、符号学等等,或者遵循艺术与哲学形成学科交汇的作品个案探索,这方面我想方法既受制于观念,也受制于操作者的综合学养。实际上王犁和韦力的文字,研究画家或者流派,依然是以相对宏观的时代思想、社会环境,相对微观的艺术家生涯经验、美学主张、个性实验等要素为主,在这两本书里,具体作品的分析似乎不是最核心的任务,但他们的态度和能力,依然保证了抉幽发微的论文水准与实通晓畅的阅读快感。
当然,这可能是不同习惯和体系下治学方式的区别,沈语冰老师的学术框架相当部分来源于西语哲学,如同即将来临的阅兵正步,受胎于普鲁士阅兵式,而王犁发端于笔墨,韦力发家于版本,这种根性的思辨本能,大约是没有轩轾之分的,毕竟,只有我们今天的正步,才敢放心的说,是正义的脚步。
2025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