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构王朝中追问历史书写真相 王若虚推出新书《遗神》

8月16日,青年作家王若虚围绕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遗神》在上海举办了两场新书分享会。活动聚焦《遗神》中“小说裨”的独特设定、架空历史的构建逻辑,以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边界探索,揭开了这部融合悬疑、历史与推理元素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轨迹。

从“采风者”到“破案人”
《遗神》的核心魅力,始于主角曲少毫“小说裨”的特殊身份。在书中虚构的东扬国,“小说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虚构写作者,而是负责搜集民间舆论、记录市井动向的底层官吏——这一设定源自王若虚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小说家”的重新发掘。
“古代小说家与现在的小说家是反过来的,更加类似于舆论的搜集者,可以去道听途说,最后把听到的信息整理出来再报上去,属于一种非虚构的性质。” 王若虚在分享中解释,这种“功能倒置”的设定,让曲少毫既是案件的调查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从‘小说裨’到‘核监官’,他既是断案人也是记事者,最后写下了一段属于无名之人的历史”。
“小说裨”的设定让作家阿来想到了他创作的《尘埃落定》中负责记录当权者言行的书记官,他指出“小说裨”的职能与古代采诗官、史官形成微妙对照:“采诗官搜集社情民意以达天庭,史官记录帝王言行以存史,而‘小说裨’记录的是民间的‘八卦’,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细节。”
推理小说研究者华斯比则认为,相较于传统推理小说中“记录者即助手”的模式,曲少毫的“小说裨”身份让“书写本身成为破案的武器”,“他的笔既能成为证据,也能成为把柄,这种设定在推理文学中是极具突破性的。”
在平行宇宙中追问历史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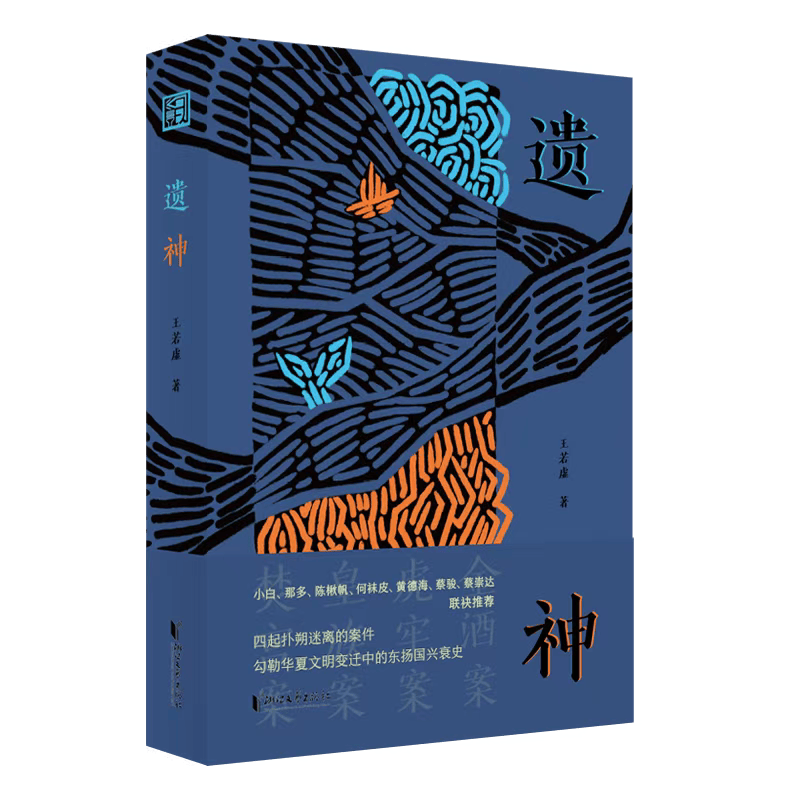
《遗神》的另一个大胆尝试,是构建了一套从真实历史中分叉的“影子王朝”。故事以秦始皇博浪沙遇刺事件为节点——假设刺杀成功,历史由此转向,最终在14世纪形成了一个名为“东扬”的虚构国度。
王若虚将这种创作比作“危险驾驶”:“传统历史小说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路线既定;纯架空小说又像在天上飞,自由度极高;而《遗神》是两者结合,既要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又要在细节处制造合理的‘分叉’。”
为了让这个架空世界落地,王若虚付出了“自虐式”的努力:从博浪沙事件(公元前200多年)到14世纪的东扬国,他需要梳理近1600年的“平行历史”,小到官职体系,大到权力结构,都要符合逻辑推演。阿来对此深有感触:“创造一套完整的官制、社会体系,比写真实历史更难,这相当于重新设计一个文明的骨架。”
这种严谨让架空历史获得了独特的真实感。华斯比提到:“书中的东扬国看似虚构,却处处可见秦、汉、宋的影子,这种‘熟悉的陌生感’让历史悬疑更具张力——你知道它不是真的,却忍不住相信它可能发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