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明中期前后七子的书法美学观
明中期前后七子,是文学概念下的统称,但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潮(实质上是文学界的“复古”思潮),也必在他们的书画观上反映出来,这一篇,我们来学习明中期前后七子的书法美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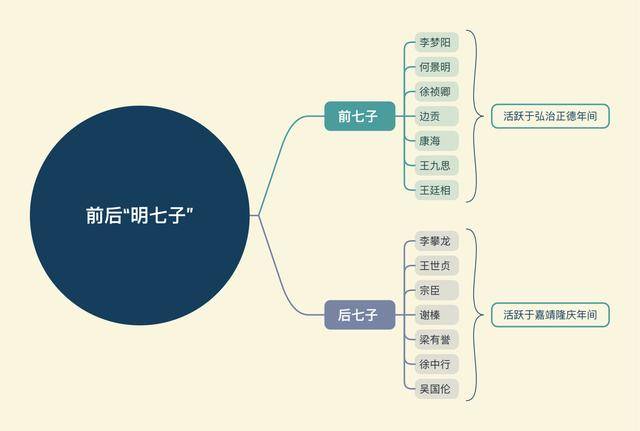
明代中期前后七子
一、李梦阳的书法审美观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省)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

李梦阳像
《明史·文苑传》称:“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记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段文字十分概括地表明了前七子复古思想的基本宗旨。以书法比较,祝允明“沿晋游唐,守而勿失”的观点最为似之。
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中期的重要作用,一是以复古阻断程、朱理学对文学艺术的统治势头,二是以模拟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来廓清明初台阁体给文坛带来的庸俗之风,以追求高古的格调,这样,在当时势必带来一种新鲜的文风。
在书法方面,我们看到从吴宽、沈周起即向宋代苏轼、黄山谷学习,至文、祝对宋代写意的书风都加以肯定,这就打破了程、朱理学鄙视苏、黄、米的戒律。到祝允明,更反对学古便是奴书的观点,力主追“根源”,将宋人之根源与晋唐紧紧勾连,以复古倡导“察其祖宗本貌”。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吴门书坛的复古运动与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其宗旨及作用是基本一致的。
前七子所谓“诗必盛唐”,“作诗必须学杜”之论,原有“取法乎上”之意,如同书法中“书不入二王,徒成下品”之言一样。故在李梦阳的笔下,第一位是重古法。李梦阳曾多次以书法比之文法、诗法,他在《驳何氏论文书》中称:“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者,固法也。”又云:
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非笔之精也。精者何也?应诸心而本诸于法者也。不窥其精,不足以为字,而矧文之能为?文犹不能为,而矧能道之为?
李梦阳关注古法,在历代复古派的观点中当属最为典型的一位,对于书法的态度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已讲得十分清楚。所谓“不窥其精,不是以为字”,即是说不通古法何来欧、虞、颜、柳?因此,个人创造和古法之间,他首先考虑的是对古法的尺尺寸寸守而勿失。进而他更认为只要做到“窥其精”,至于能否“自成一家”则无所谓。在《再与何氏书》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云:
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自立一门户,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杨邪?此亦足以类推矣!……仆非知诗者,剧谈偏见,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读子昂、必简诗,庶获不远之复,亦知予言之不妄。不然,终身野狐外道耳。
李梦阳以书法中的摹古,比之诗文中的拟古,自是一种很特殊的观照。
他以书法临摹要求“似”,来强调诗文中的拟古也不必去考虑被别人讥笑,这与祝允明反对“奴书论”的观点很有点相似的味道。然而他将学古与“自立一家”完全对立起来,却是十分狭隘的观点。他所强调的古法,具注重古法的程式,而忽略古人的创造,认为后人只须尺尺而寸寸守其程式,并不存在“舍筏登岸”,“法为我用”的问题,因而更无须“自立一门户”,如果“自立门户”,则终身为野狐外道了。
必须指出,李梦阳的这种观点,在前七子中亦是十分极端的,所谓“矫枉“而太“过正”了。在当时,他的这种观点已为七子中的何景明驳斥。至于与书法中祝允明的观点比较,亦并不一样,因祝允明反对“奴书”论,毕竟还是主张“先随人后”而后“不随人后”的。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的首领,上述观点当然影响很大,发展到后来,必然出现另一种倾向,尤其是他们“汉后无文,唐后无诗”的观点,使学者产生错觉,误将学古、摹古当为惟一的目标。于是复古被摹古、拟古所替代,古法的规矩,成为扼制艺术创造力的枷锁,甚至模拟前七子的风气也开始抬头。文坛上的这种风气,在书坛上的表现,则体现在吴门四家后,吴门书家往往以文徵明效仿对象,诚如莫是龙所指出的那样:
“吴中皆文氏一笔书,初未尝经目古帖,意在佣作,而以笔札为市道,岂复能振其神理、托之豪翰,图不朽之业乎?”这样的吴门书家当然不再如祝允明那样去追“根源”,“察祖宗之面貌”,于是成为无源之水的吴门派末流开始走向衰退。
二、王世贞的书法美学观
关于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我们在前章吴门书派中已有论述。王世贞在前后七子中,学问渊博,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的影响,亦要远胜于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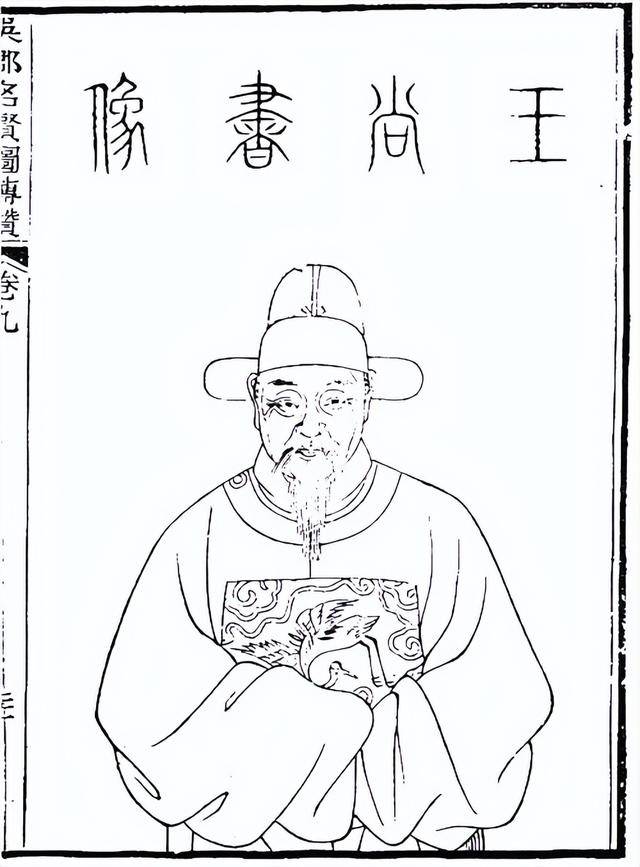
王世贞像
尽管作为前后七子的主要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主调仍是复古,甚至他还有过大历后书勿读的主张。然而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有所变化,在《宋诗选序》中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以为宋、元之诗亦有所取,以至病极重时还在讽诵苏东坡的诗文。
王世贞在四十岁前著有《艺苑卮言》,这部著作以论诗主,而附录中亦有论书。我们通常在书论中读到他的《艺苑卮言》,实是他论诗后的附录。此外,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弇州山人书画跋》,其中的书法题跋,亦是其书法思想的主要体现。在《艺苑卮言》的论诗中,他曾提出这样的学诗主张,云:
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后,方足覆瓿。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所谓“师匠宜高”,如同后人所云“取法高古”,但他的“捃拾宜博”却限止于唐代贞元年(关于这个贞元,或说是唐德宗年号,或可称唐太宗的“贞观”和唐玄宗的“开元”合称)以前。贞元以前为之盛唐,盛唐以后的诗,他认为无可取法,直可以用其去覆盖酱缸了。
有趣的是,《艺苑卮言》的论书中,我们不仅没有见到这样极端的主张,相反却已经看到了他在晚年诗论中才具有的“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观点。他引古代书论,从南朝到元代,从元代到同时代的杨慎、丰坊,有可取者皆录之。他评论古代书家亦不以时代偏废,尤对自己所熟悉的当代吴门书派作实事求是的评论,当然他的评论中,自有自己的标准,请看他评宋人书:
宋初王待诏著、宋宣献(按:即指宋绶,谥宣献)、李西台、苏参政皆称名书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评待诏如小僧缚律,西台如讲僧参禅。然待诏犹有晋人意。范文正《伯夷颂》见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苏长史皆学怀素,杜瘦而生,苏瘦而弱,第觉玉润微胜冰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滞而不大畅。苏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行草稍自结构,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黄山谷大书酷仿《瘗鹤》,狂草极拟怀素,恣态有馀,仪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终愧大雅。是四君子者,号为宋室之冠,然小楷绝响矣。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既注意到王世贞客观的评价,所谓得失兼顾,又注意到他特别突出了“古法”的重要,对于古法少逊而仍知法古者,如王著,他称“犹有晋人意”,可见他于书法不仅仅看其是否得法,即若蔡襄“略取古法”,他一样也批评其“稍滞而不大畅”,而苏东坡他则认为“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可见他不仅重古法,也同样重视书法的意趣。
不过这意趣是以“古法”为“雅”的,而“古雅”的典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如果在文,他认为是西汉,在诗,他认为是盛唐,那么在书法他实际上提出了魏、晋、宋、齐。他写道:
智永不能脱僧气,欧阳率更不能脱酸馅气,旭、素、柳、赵吴兴不能脱俗气,南晋(按,指东晋)、宋、齐之间脱矣。
他还曾于《淳化阁帖十跋》中云:
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割石,犹足压倒馀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
由此可见,王世贞虽未在书论中如文论般说出“贞元而后方足覆瓿”的极端语言,但实际上他心中书法古雅的批评标准仍如文论一样,有着一把尺子,这就是“魏晋”。所不同者,他于书法说得更客观一些,凡合古法又淳雅、秀雅、典雅、精雅者皆给以肯定,并且可以看到他的古雅还包括了“天趣、意、韵、气、风骨”的成分。
然而虽合古法却失之偏颇的书法又都在他的批评之列。如他评张风翼云:“伯起生平临二王最多,退笔成冢,虽天趣小渴,而规度森然矣。”评李邕、赵孟頫云:“北海伤佻,然自雅;文敏稍稳,然微俗。”评邓文原云:“邓文原有晋人意,而微近粗。巙巙子山有韵气,而结法少疏。”因此又足见他的“古雅”,十分精细而缜密,凡过犹不及者,都不合他的标准,而这把缜密的标尺,正来源于魏晋的书法审美观。在他的书论中曾多次抨击唐末亚栖、辩光和本朝解缙、张骏等人的草书,正是因为这些狂怪乱野之作,不合他的“古雅”标准。
有重要意义的是王世贞不像李梦阳那样反对“自立门户”,他还强调自成一家和“变”的价值,重视继承和“损益”两个方面的意义。如云:
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吉法损益。自成一家。若赵承旨则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已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
(祝允明)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
(文徵明)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
王(宠)正书初法虞永兴、智永,行书法大令,最后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动人。文以法胜,王以韵胜,不可优劣等也。
右军之书,后世模仿者仅能得其圜密,已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紧势游力,淳质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绳其祖武也。欧、颜不得不变其真,旭、素不得不变其草。永、施之书,学差胜笔,旭、素之笔,笔多学少。学非谓积习也,乃渊源耳。
“变”的概念,在王世贞的笔下,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变”必出自渊源,二是损益古人虽有主动、被动之别,但变为时代之规律,此所谓“不得不变”。正是出于这样观念的支配,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贞在评论当代书家和吴门书家时,投以积极的热情,“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他在众多吴门书家中拈出三位,并给以高度评价,大约也正说明他的书法思想与吴门派这三位的书法追求最为契合。因此我们认为王世贞的书法思想既是后七子的美学观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是吴门书派书法美学观的一种体现和总结。
三、其他诸家书论
1、杨慎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这位就是《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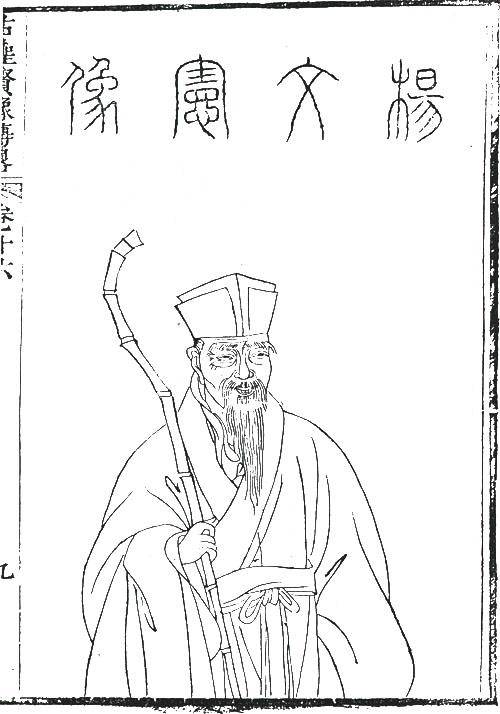
杨慎画像
杨慎曾著有书法论著《墨池琐录》《书品》等。
他主张书法崇尚晋人羲、献,说:“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赵子昂出,一洗颜、柳之病,直以晋人为师,右军之后,一人而已。”这种观点,与七子文论所言“大历后无诗”的观点何其相似,不过他的许多评论,也并非仅推重赵孟頫一人,如称蔡襄“字有晋韵,在苏、黄、米之上”,又称“本朝书法家当以宋克为第一”,可见其批评标准在有无晋韵,并因此标举“婉媚”与“蕴藉”,反对抛筋露骨而失韵。
2、何良俊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

何良俊画像
其所著《四友斋丛说》第二十七卷为论书,他虽与杨慎地处两地,但在崇尚二王晋法和推崇赵孟頫上几乎无异,此亦可看到当时书坛思潮的主流。他说:
宋时惟蔡忠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直到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
当然他尽管如此说,却不因此而对后世书法和当代书法大加鞭挞,而是多见赞语。何良俊自倭寇侵扰后,移居苏州,与吴中书家文徵明、王宠等多有来往,称“自赵集贤后,集书之大成者衡山(文徵明)也”,“衡山之后,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
从杨慎和何良俊也可看到嘉靖间的书法审美观,大体与文论中前七子相仿佛,在书坛上则与吴门派同调。
3、丰坊
丰坊的简介可见190课,丰坊曾著有《书诀》一篇,王世贞《艺苑卮言》和其他题跋,曾有多次引用,并称为《笔诀》,实即为一篇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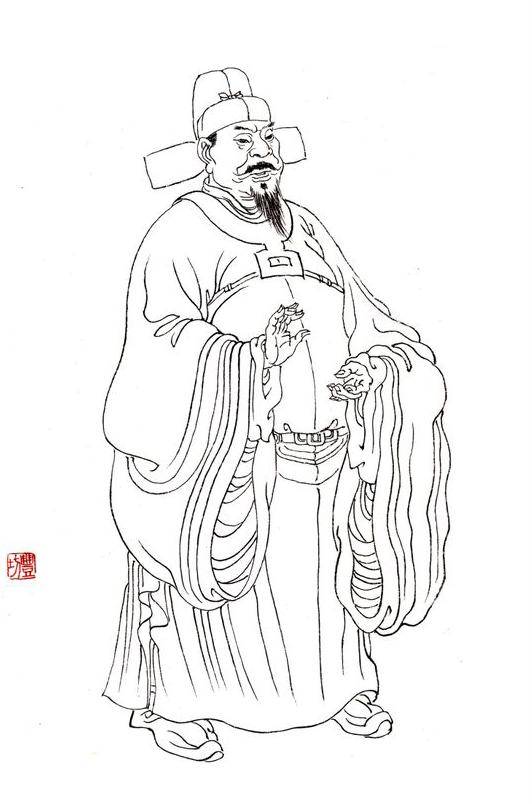
丰坊画像
《书诀》大抵是丰坊总结先贤论用笔之说,加以阐释,体现了他通过笔法研究重视学古的追求。此外丰坊另有《童学书程》一篇,称得是部书法教科书,各种书体除列出临摹范本外,亦略有评说。在《行书》一节中他写道:
学行书以二王为祖宗,而魏、晋为羽翼。
行书大者,唐以前极少⋯⋯米元章过于豪放,古意渐泯。王黄华、张圣之遂为恶札之祖,元赵子昂、鲜于枢、崾子山等,乃有可观。
盖唐、宋以来,得二王之法者,赵公一人而已。
这种论调与杨慎、何良俊几乎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丰坊一方面标举二王,推重古法,另一方面,则敢于对明前期的书法展开批评,尤可看到他痛恨两种类型,一为豪无生气之台阁体,二为不要古法任情恣性之野狐禅。而这两个方面的攻击,正是明中期以来书坛所肩负拨乱反正的职责。在《楷书》一节中说:
惟近世沈度、姜立纲等,俗浊之甚,在所痛绝。
另外,丰坊又于《草书》一节中说:
书横卷小幅,宜守规矩,必法二王,书悬轴大幅,则尚雄逸。旭、素、彦修雄逸之尤者也。元惟巙子山、本朝惟宋仲珩最得其法,以其从二王规矩中来,而化以旭、素之错综,故能度越诸子。近时张东海之学,缠绕无骨,备死蛇结蚓之态;李西涯之行,怒张无体,创缩头长脚之形,时俗趋之,更成画虎,此古法所以益远也。
丰坊的这些论述,实在是不乏精彩之处的。他痛斥沈、姜这两位台阁体代表书家的楷书,当然是批判程、朱理学给明初带来的危害,此正与七子论文指向相同,且并不像吴门、松江诸家多少有乡情在,谈起沈、姜来,有一种自豪感。在推重康里巙巙和宋璲而鞭挞张弼、李东阳的草书时,也可看出他并没有带上地域感情的有色眼镜,而其批评标准正在复古——从二王规矩中来。他的批评虽言辞激烈,却并无偏见,如称李东阳之行书“怒张无体”,但评其篆书则赞曰“一扫敝习,追踪古人,其篆法之中兴欤”。他的这些思想基本上是与当时文坛前后七子思想一致的,根本的宗旨就是以复古矫正书坛凋疏之弊,借古开今。所以王世贞尽管恶其人,但对他的书论却十分欣赏,也足可看到他们的审美取向是相同的。
其他书论还有:
被王世贞列为末五子的屠隆(1543-1605),有《考槃馀事》四卷。其论学书与评国朝书家,几乎与王世贞同调。又如孙鑛,字文融,号月峰,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孙鑛(kuàng)著有《孙月峰评经》在当时十分风靡。他曾以王世贞《弇州山人书画跋》为底本,进行再评论,是为再跋,故名《书画跋跋》。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以其评经之观点认为孙鑛堪称是“七子文论之后劲”。也就是说孙鑛虽已是活动于万历时期的人,但其文艺思想仍受到王世贞的影响。从其所著《书画跋跋》而言,大体推崇王世贞的跋语,以崇古为尚,同时主张复古通变,与王世贞观点皆相去不远。但孙鑛的书跋中还主张“天趣““作字贵在无意”,与他评经论文之主张一致。这一点似与后七子观点是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