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晶:“生活流”的情节艺术与人物刻画(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之五)
红楼梦艺术的超越于传统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生活流”的叙事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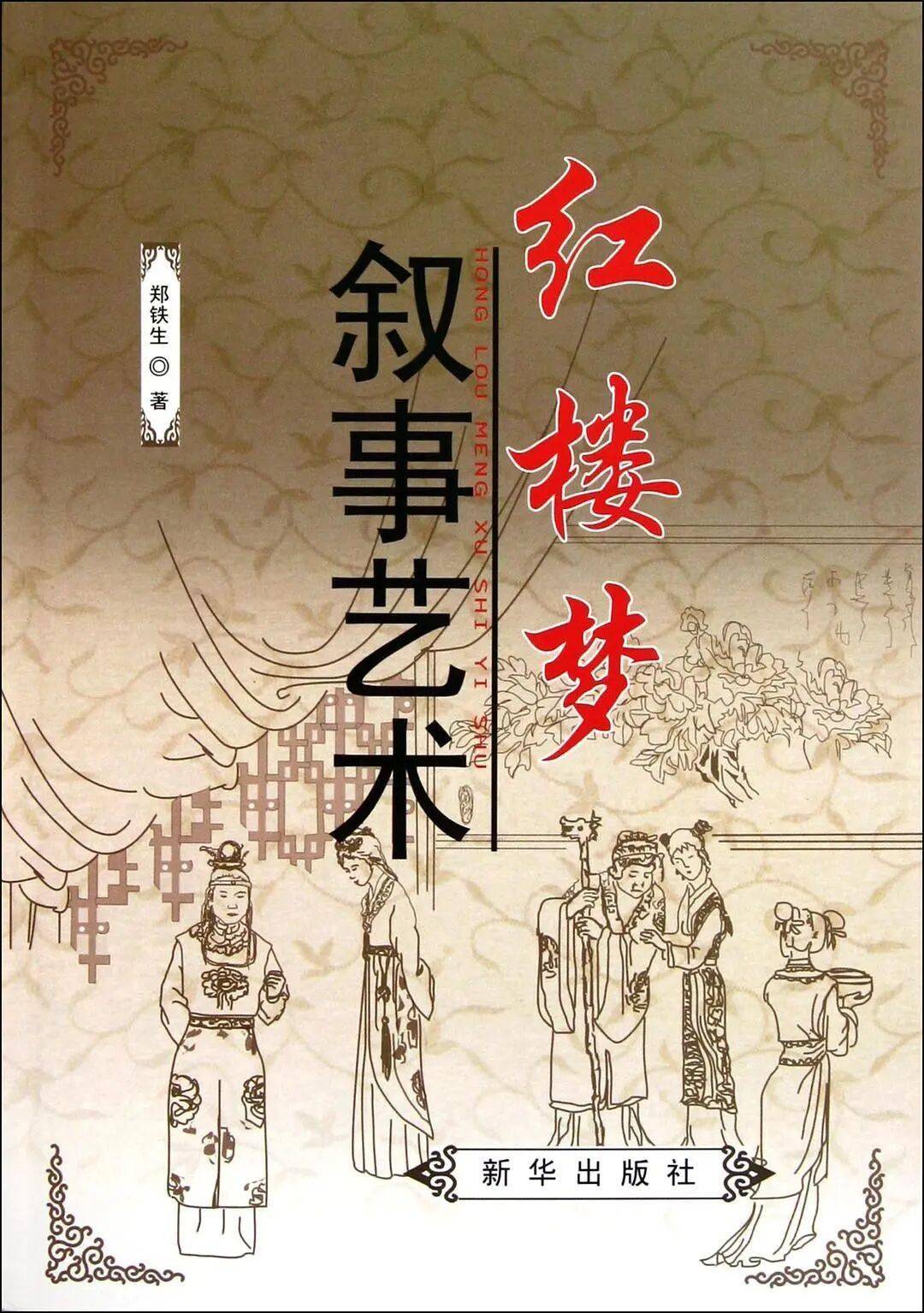
《红楼梦叙事艺术》
关于这种“生活流”的艺术内涵或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第一,在情节方面,生活流的情节艺术并非如传奇小说一样,只有几条粗“梗”,它的情节线条或走向几乎就是其生活流动本身,情节、细节随生活现实的展开而展开,作者并不需要如传奇小说一样,去特意设计安排矛盾冲突,它的矛盾冲突和故事就自然涌现在生活的自然流动中。
因此,红楼梦的情节艺术还呈现出与此相联系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他的情节就像一棵大树,旁逸斜出,枝节横生,特别丰茂。
它的每回书,虽然在表面上往往也有着一个对称性的回目名,但其实,作者并不严格按着回目所提示的两条大梗组织运行故事,其回目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甚至只是一个浮面的名称而已,实际的情节往往纷繁多彩,大大超出于回目之上。
第二,这些在生活的自然流动中涌现出来各种事件、故事、矛盾冲突等并非如某些读者所认为的那样,就是一本生活的流水账,就是闻见毕录,写一些吃喝玩乐等琐碎小事,其实作者往往是在这看似随意的生活流式的情节、细节的展开中,刻画出鲜明的人物性格,表现出深刻的人性,写出社会的人情世故和伦理冲突的。
在这种“生活流”的叙事中,作家其实是有着精严的选择的,只不过他的选择不是如传奇小说一般以传奇惊悚为目的而进行选择,而是在真实的生活流的基础上,以是否表现出人性、是否能够刻画表现人物性格,是否能表现其深刻的主题为标准的。
因此,这种生活流的艺术,不仅不是一堆生活的杂碎,而是含金量极高,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来说明,或许最为恰切。
第三,由于书中的情节、细节是随生活流而自然而然而展现流淌出来的,再加之作者具有很高超的写实手段,对生活的情节、细节及人物语言等把握得十分精准到位,因此,他往往能够把这些自然涌现出来的情节细节写得活色生香,触处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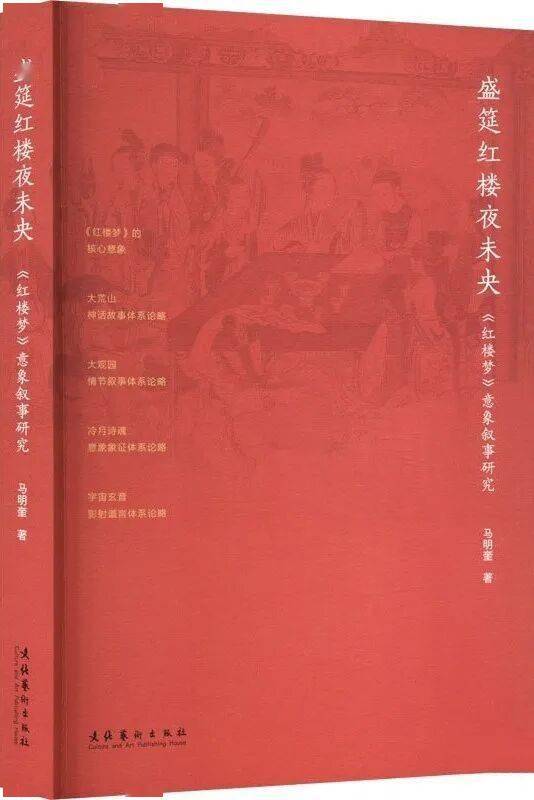
《盛筵红楼夜未央:红楼梦意象叙事研究》
这三点,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生活流”艺术的三大特点。我们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先生赞扬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八字的深刻意义。
下面,我们仅以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作为标本进行分析解剖,来说明红楼梦的这一“生活流”的叙事特点,最后,我们将对曹雪芹“生活流”的艺术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一些总结。
红楼梦第16回,从其回目名来说,主要要写两个故事,一个是元春选妃被选中了,第二个就是宝玉的好朋友秦钟不幸夭折。
不过这一回书,真正重要的,只是前一个故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一个故事在写,或许只是为了章回小说的标题需要对称的原因,加了一个秦钟夭折的故事,当然,秦钟夭折的故事在其中也并非全无意义。
下面,我们还是回到第16回的文本,看曹雪芹怎样在这两根大梗或者就是一根大梗中来展示他那超绝的叙事艺术:

赵国经、王美芳绘金陵十二钗之元春
第16回元春选妃命中的第一段情节就十分耐人咀嚼,这段情节是什么呢?就是夏太监刚来到贾府“降旨”的时候,贾府合家那种栗栗危惧的情状:
忽有门吏报道:“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吓的贾赦贾珍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香案,启中门跪接。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那夏太监也不曾负诏捧敕,直至正厅下马,满面笑容,走至厅上,南面而立,口内说:“奉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吃茶,便乘马去了。贾政等也猜不出是何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
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有两个时辰,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报喜,又说:“奉老爷的命:就请老太太率领太太等进宫谢恩呢。”那时贾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聚在一处打听信息。
这是小说似乎出人意外的第一个情节,它没有写特大喜讯,合家庆祝,更没有如某些全知叙事的小说一样,想当然地编排出一些宫中选妃的隆重情景,而是写了贾府合家人那种未知的恐惧。
但是我们细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的显现,是真实的生活流的一部分,这种忠实于生活的写法,虽然在表面上似乎不合套路(传奇小说的套路),也与第十六回的回目名称不甚相关,但是它却是高度真实的,更合乎逻辑的。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掌握着绝对生杀予夺大权而且喜怒无常的皇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给你降下灾祸,更兼曹家虽然显赫,但终究不过是满人的一个包衣奴才。
《太监往谈录》
此外,太监扰乱宫廷,祸害社会,也历来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大特征。小说后来还在其他地方写了太监、夏太监来扰乱贾府的故事。
因此,第16回一开篇就写贾府合家栗栗危惧的情景绝对是真实的。此外,它不仅是真实的,也更是有意义的,他写出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当然也显示出了曹雪芹那天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出了他那远超越于时代的思想境界。
此外,从情节上它还高度照应着第105、106、107回贾府那部抄家“大戏”:如此天大的喜事整个贾府竟然吓得如惊弓之鸟,以后真正的灾祸来了当何如之?
那么,第十六回开篇的第一个情节,是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呢?不能这么看,作者选择什么写,以及怎么写,还是经过选择的。

《中国叙事学》第2版
首先,即使它是生活流的一部分,是一种真实的再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生活现实”,肯定不只有这一种现实,而作者选择这一种现实来写,却还是基于主题的表现,基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基于作家的境界,并非只是某种现实的必然。因此说,虽是所谓“生活流”,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被动地堆积生活素材。
由于开篇这一个情节只是刻画了一个人物群像,并无单独突出的人物,因此在这里我们对其人物刻画问题略,但贾家合家上下那种栗栗危惧的情景还是被作者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我们如果联系第105、106、107回贾府被抄的情景看,就觉得它十分真切准确地传达出在封建社会,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心理和情形。
第16回第二个有意味的情节就是描写在贾府的天大喜事中,曹雪芹不是着力描写人们怎样欢天喜地,怎样高兴得找不着北,而是描写贾宝玉对此的漠然视之:
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你道什么缘故?原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来找秦钟,不意被秦邦业知觉,将智能逐出,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气的老病发了,三五日,便呜呼哀哉了。秦钟本自怯弱,又带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见老父气死,悔痛无及,又添了许多病症。因此,宝玉心中怅怅不乐。虽有元春晋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闷?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细问原由,方知贾雨村也进京引见,——皆由王子腾累上荐本,此来候补京缺,——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徒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茔了,诸事停妥。贾琏这番进京,若按站走时本该出月到家,因听见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问了黛玉好,馀者也就不在意了。

邮票《元春省亲》
这第二个情节,虽然也仍然大致扣着回目名中的那个大梗,在写贾家的大喜事,但是它似乎又不那么合传奇小说的“情理”。
按传奇情理来写的话,它应该写贾府怎样合家欢庆,怎样大操大办等,不会写得这样落寞寡淡。
但是,这恰恰是更真实的,更生活化的,也是更有意义更有境界的。从其生活真实的角度看,宫中险恶,幽闭于深宫,元春选妃成功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此外,此时的宝玉还是个孩子,元春成了皇帝的妃子,又关他什么事呢,况且此时他的好朋友生病,黛玉又不在家,他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以上是从生活真实的角度观察。
但是,对于这个情节,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当作是一个简单的现实的写真,它实际上是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曹公的创作倾向,表现出作品的主题。他就是要用这种含而不露的手法 ,表现出他的情感观念,表现出他那远超于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

赵成伟绘贾宝玉
因此,宝玉这种对整个家族似乎“天大喜事”的漠然视之,被众人视为“越发呆了”的行为,恰恰是非常好的刻画了宝玉这个人物,也表现着整部小说那人道主义的主题。
这个主题(之一点)就是,一个年青女子,亲情相隔,囚在深宫,并非什么好事。以后我们在第18回元春省亲的故事中,也会看到小说通过元春之口以及那种悲戚的情景描写,感受到作者表现的这一主题。
所以说,作者采用的这种“生活流”的写法,看似随意,其实并非随意的,仍然是经过作家选择的,是作家的思想和境界的体现。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部红楼梦中,主要运用的是限制视角,而在各个限制视角中,以贾宝玉的视角进行叙事,又是最主要的限制视角,因此,在贾府如此重要的大喜事中,贾宝玉对此半点不关心,形同“呆子”,也是宝玉视角的必然结果。
第16回第三个有意义的情节或细节,是黛玉回来与宝玉刚见面的那一场面:
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错,果报:“琏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见面时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场,又致庆慰之词。宝玉细看那黛玉时,越发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忙着打扫卧室,安排器具,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鹡苓香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暂且无话。

刘旦宅绘《宝黛读西厢》
这一情节或细节,严格讲,与回目中所提示的故事似乎更不搭界,黛玉奔丧回家如何如何,回来又如何如何,与贾家此时的大喜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红楼梦的情节艺术的一大特征,即在生活流中自然展现情节、细节,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种写法,与传奇小说的情节艺术是很不同的,传奇小说的情节,那是亦步亦趋,步步都要踩在那个主要情节的“梗”上,而红楼梦这样的“生活流”小说,其情节艺术则要自然纷繁丰润得多,它可以紧扣一条主线,也可以若即若离。
当然,其纷繁丰润也决不是随意的。譬如,第16回这里写黛玉,虽然与此回故事的大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从小说情节和人物刻画的整体来说,它却是与整部小说对黛玉的人物刻画和宝黛爱情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就此方面言,此处描写至少在几个方面具有意义:
一,说明黛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飘逸风采了,是一个花蕾初绽的美少女了。

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剧照
第二,初次写黛玉拒绝宝玉的礼物,并且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一方面说明了黛玉那种孤高的性格,也说明了她性别意识的觉醒,而在此之前,黛玉虽然孤高自许,但或是没有什么男人女人之分的性别意识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苏醒,也是黛玉性格成长的一部分,也是推动宝黛爱情发展的一部分。
第三,这一细节还说明,黛玉对待爱情的特点,就是特别专一,她喜欢宝玉,难道宝玉就不是男人吗?所以,她所说的“臭男人”只是指别的陌生的男人、她不知心的男人,是并不包含宝玉的。不仅不包含,反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她对宝玉爱得专一。因此,这一个似乎脱离于叙事主干的情节、细节,非常好地刻画了黛玉性格的特征及其成长。
从这一个生活流式的情节手法我们可以看出来,某一个生活流式的情节的运用,它并非如传奇小说一样,会按照情节的大“梗”而亦步亦趋,它可以依据真实生活本身的流动,而有机地展开或穿插。当然,这种情节的有机运用,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过的,却也并不是随意的。
第一,它必须是这个生活流的自然的一部分,第二,它必须服从于人物性格的刻画,第三,这种性格的刻画又是整体人物性格刻画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一种人物刻画的网状特征。
此外,所引部分,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黛玉一骂一掷,却非常有神韵,以至于它成了表现黛玉性格的一个经典桥段。这种随自然情节而闪现出来的生香活色,也是这些似乎脱离主干的情节之所以成立的重要原因。
记得外国的某位小说家说过,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牵引着读者不断地追问“以后怎么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悬念,红楼梦当然也有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成长变化,但它却并不或并不主要靠这类悬念吸引读者,而是靠每一个自然出现的故事、场面,以及作者对这些故事场面那种触处生春的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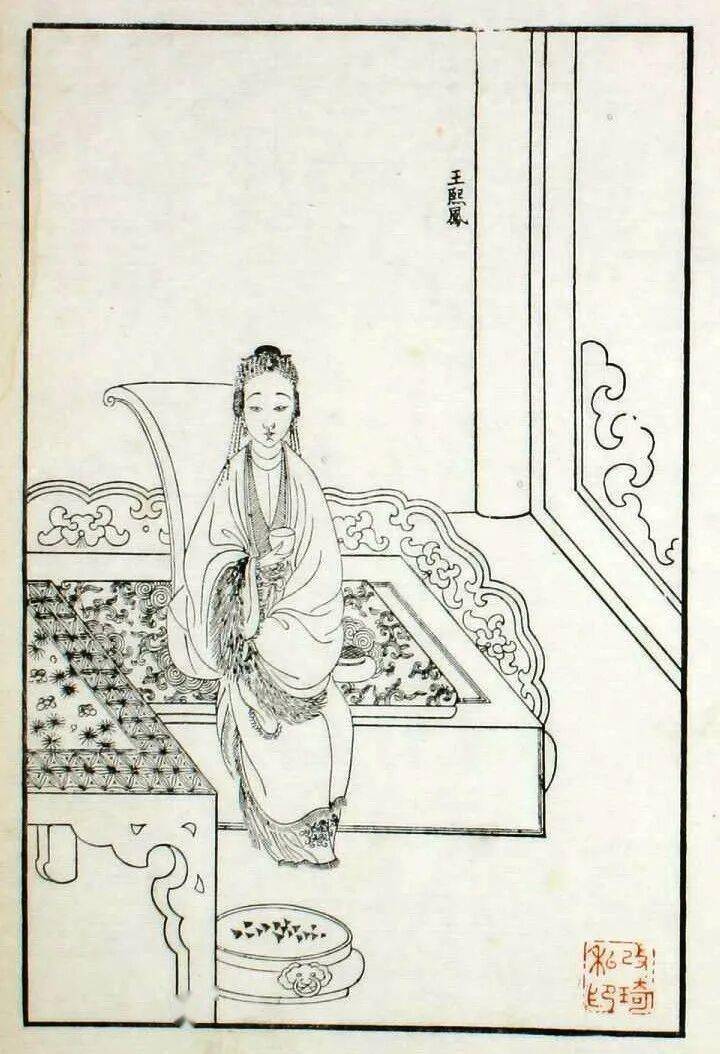
《红楼梦图咏》之王熙凤
第十六回第四个有意义的情节就是王熙凤在贾琏从苏州刚回来时的一番嘴舌卖弄:
且说贾琏自回家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事繁,无片刻闲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因房内别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见毕,端上茶来。贾琏遂问别后家中诸事,又谢凤姐的辛苦。凤姐道:“我哪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

邮票《凤姐设局》
从情节上来说,第16回的这段情节也是脱离主干的,与回目名称所标示的故事最多也是若即若离,但是它的出现很自然,并没有给人以离题之感,对于人物性格刻画,它也具有意义。
这一番嘴舌卖弄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以及弄权铁槛寺等情节之后,一,它说明了凤姐作为妻子,在丈夫长时间外出归家后那种禁不住的喜悦,第二,它又像所有女人一样喜欢卖弄自己的口舌,第三,元春选妃成功又使她对夫家对贾琏多了一份谄媚,第四,她还沉浸在协理宁国府的巨大的成就感当中,而这一点又是自己的丈夫不知道的,但是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自己夸自己,于是来了一番正话反说。
凤姐的这一番嘴舌卖弄,写的很生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刻画出了凤姐性格的多样性,她也并不是一味好强,在某些时候,也表现出一点“小女人”的特性,虽然或有做作痕迹。此处的描写,与整个小说中的对凤姐这一人物的刻画紧密相关,它们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叙事网络整体。
第16回第5个有意义的情节是贾琏和凤姐的一段对话:
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说话,凤姐便问:“是谁?”平儿进来回道:“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打发她回去了。”贾琏笑道:“正是呢。我才见姨妈去,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刚走了个对脸儿,长得好齐整模样儿。我想咱们家没这个人哪,说话时问姨妈,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头子,叫什么香菱的,竟给薛大傻子作了屋里人。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她!”
凤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苏杭走一趟回来,也该见点世面了,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她,不值什么,我拿平儿换了她来好不好?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时候,他为香菱儿不能到手,和姑妈打了多少饥荒。姑妈看着香菱的模样儿好还是小事,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儿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才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给他做了屋里人。——过了没半月,也没事人一大堆了。”一语未了,二门上的小厮传报:“老爷在大书房里等着二爷呢。”贾琏听了,忙忙整衣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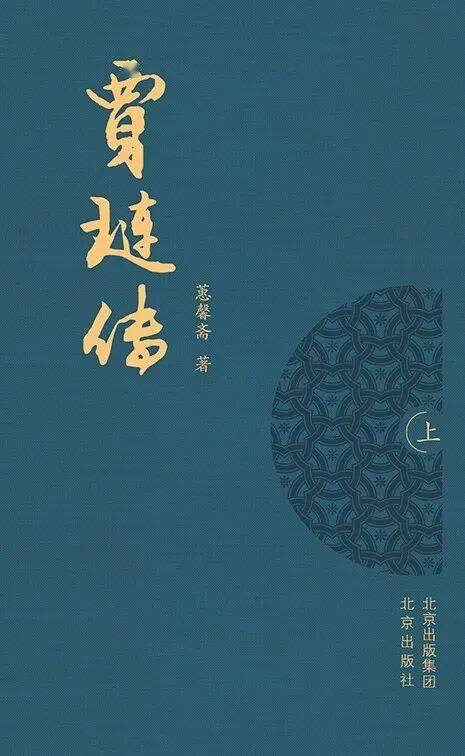
《贾琏传》
从传统的角度看,它无疑也是偏离主干的,与回目名也不相干。但是,它出现在第16回,却也自然而然,这就是因为它是真实生活流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并非是毫无疑义的生活的流水账,它与前后的人物刻画和和情节等因素自然相连。
就其具体功能来说,这段对话就联系前面继续刻画了香菱,也表现了贾琏的好色特性,也借机补写了薛蟠霸占香菱的情节。 而这些情节及其人物刻画,也都是如上所言,与回目中表面的两个叙事主干并无必然联系,但它们都是这种“生活流”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6个有意义的情节是平儿对凤姐撒谎,又从一个侧面写了王熙凤私自放债的劣行,这类情节,一直到第105回被抄家,都是断断续续地在写,这一方面写出了凤姐的贪婪,也写出了贾府败亡的根源之一,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7个有意义的情节是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趁贾府办大事来求王熙凤给她的儿子找份差事做。
从情节联系上来看,除了第一个情节,一直到第七个情节,才自然出现与元春省亲直接相关的情节,但即便如此,它也并非写元春省亲本身,而主要是写了王熙凤的霸道、能说会道,写了贾琏偷腥的习性,写了赵嬷嬷走关系的老到和能说会道,还通过赵嬷嬷的回忆把元春加封为贵妃省亲和历史上“王家”以及“甄家”“接驾”的盛况联系起来,同时暗暗地写了皇家耗费民脂民膏的“罪过”。
这些内容本身,虽与主干显得若即若离,但他它显然是更有意义的,显示出作者虽然采用的是所谓“生活流”的写法,看起来甚是随意,但实际上它是别有匠心的,有严格选择的。
第8个有意义的情节,就是贾蔷和贾蓉借着贾府要营建省亲别墅的事来向贾琏请示,这个情节虽然与元妃的故事相关,但作者的重心却是要写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那一套人情世故。
通过这段生动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温情脉脉的人情世故中,“藏掖”着怎样的贪腐文化,同时也把在这种人情世故和无处不在的贪腐文化中的人物性格表现得细腻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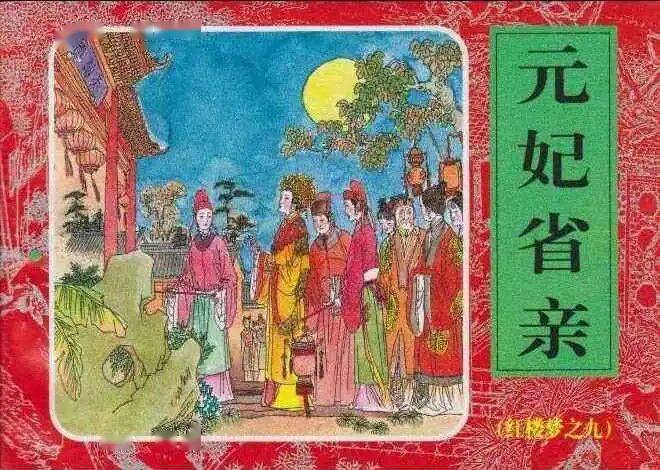
连环画《元妃省亲》
从以上我们对第16回的一些重点情节和细节的点评中,可以看出,红楼梦的情节细节艺术,是一种生活流的情节细节艺术,相比于传奇小说的情节艺术的模式化和简单化,它是有机的、自然生发的,丰富多彩的。
小说的回目名叫“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秦钟早逝的故事基本只一笔带过,就是“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的故事,它也与传统传奇小说迥然有别。
他根本不是按传奇的路子想当然地写,而是在这个名目之下,写出贾府那种“实生活”的流动,然后在这种流动中展现出人物性格、人情世故。
在这回的故事中间,写了贾府合家上下的那种不安,写了宝玉的漠然,写了黛玉的孤高、王熙凤的霸道和嘴舌卖弄,写了各种人情世故以及无处不在的贪腐文化等等。这纷繁无比的情节细节,鲜活的人物刻画,都是作家自然运用“生活流”的情节艺术方式而自然展现出来的。
当然,这种生活流式的情节细节艺术,却决不意味着它就是自然生活的一本流水账,实际上它是有严格取舍的,有精妙剪裁的,这中间或许就藏着曹公独有的大手段。

《红楼梦的空间叙事》
上面我们仅举出第16回来作为例子来看红楼梦的这种“生活流”的艺术,那么是不是只有第16回是如此呢?不是,红楼梦的每一回,基本都是这种“生活流”的叙事风格,它们就如一棵大树,各自枝条横斜婆娑,自然纷披,然而又整体相连,如此纷繁复杂统一,但又不见刻意构思的痕迹,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叙事艺术。
最后,我们想来谈谈这种“生活流叙事艺术”给我们的启示。它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真实的生活、丰富复杂的人性和人物性格以及人际关系和伦理冲突,给艺术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传统的传奇、现代的先锋、科幻武侠、装神弄鬼、向壁虚构、搞策划带节奏一类的方法写法,并非艺术的正道,至少并非康庄大道。文学创作,只要奠基于丰富的真实生活,并从中体察丰富复杂的人性、性格和复杂的关系,就能超越于一切花里胡哨的创作方法。鲁迅所说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不仅对于历史是如此,对于未来或许也仍然如此。
第二,我们要善于从红楼梦中吸取那种处理现实的方法,它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写出了人物性格,写出了深刻的人性,写出了人情世故。
它看起来是自然随意,但实际上是“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何需用刀尺”,是建立在作家的思想境界上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上的。
第三,作家的创作若要运用“生活流”的写法,要特别注意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场,你才能把它变为熟悉的“叙述场”,然后作家写起来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红楼梦长达120回的故事,极少离开大观园、极少离开贾府这个熟悉的环境,脂胭斋在批语中说:“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简,不得谓之不均也。”为什么曹雪芹叙闺中之事切,叙外事者简呢?
《〈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辨析》,谭德晶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笔者以为,曹雪芹凭他的天才直觉悟到,凭想当然地写“外事”,写自己不熟悉的事,是难以把它写到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的。我们看红楼梦,作家写的每一个人物,都如同写自己,这是因为作家对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手掌,其言语声口、音容笑貌,都如在目前,这样作家叙述起来就“不隔”,写人犹若写己。
下一篇:寻趣石景山雕塑公园的艺术与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