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上的小人物,并没有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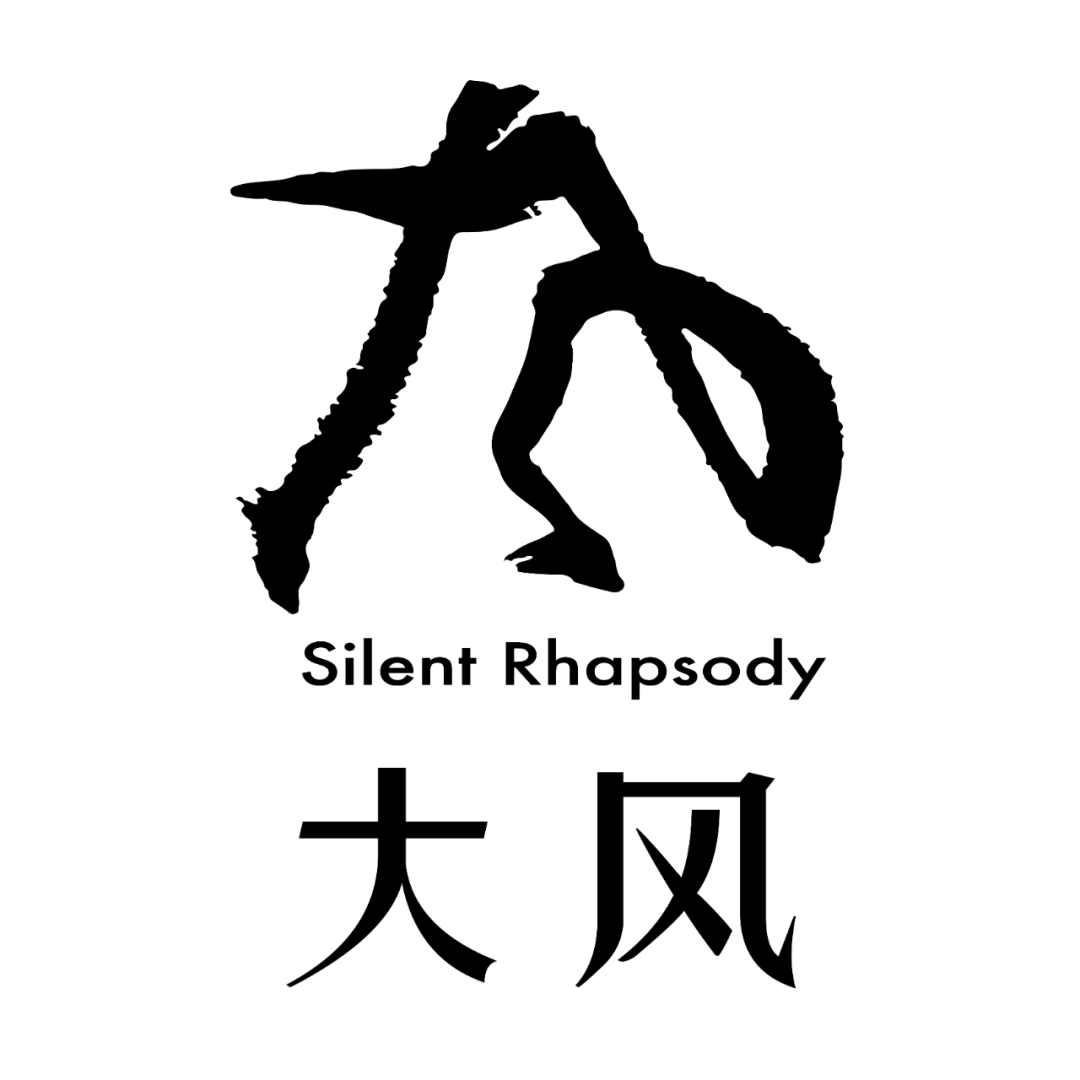
————
一本窄窄长长的粉色小书,就如同芭蕾舞者单薄纤细的小身板。德加说“我把我的心锁在了粉色缎面的鞋子里。”所以这书也用一条缎面丝带将书系起来,就像芭蕾舞者上台前系鞋带那样,拆开之后是长长的一根,既能够作书签也能更换不同的捆绑方式搭配不同造型。这个独特的丝带设计是这本书的点睛之处,打开它我们将看到一个十四岁小芭蕾舞者的故事,她就是著名印象派艺术家德加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个身影。
十九世纪的芭蕾舞者
19世纪的芭蕾舞者是一个社会特殊的存在,很多底层家庭的女孩,没有生存资源,就会被家人送到歌剧院学习芭蕾。有点像现在的娱乐公司的练习生,但远远没有练习生的地位与前途,她们绝大多数只是为了讨一口饭吃。
歌剧院的后台就是一个高级纵欲场所,拥有自己的舞女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只要足够美丽,甚至可以跨越阶级,在时尚和政治的高端圈子里发展。在那个时代文人笔下,许多出身显赫的男子为她们破产/自杀/被梅毒摧毁,说“她们拥有瓦解贵族的可怕力量”,当然这只是男文人巧言令色的甩锅,把所有罪恶的源头都归结在这些女性身上。她们就像贫民窟和经营阶层的交叉点,可以映照出出法国文化界光鲜外表下阴暗面。
本书的作者,卡米耶·洛朗斯以纪实的笔触去考证了小舞者真实的一生。小舞者生在一个巴黎底层的单亲家庭,母亲带着她们三个姊妹生活,小舞者行二,姐妹三个人先后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被送到歌剧院学习芭蕾。玛丽个头小,身体不大结实,又没有充足的食物,舞蹈练习让她筋疲力尽,当她动作不标准时,会受到老师的威胁——把她的身体锁在木箱以矫正错误的姿势。
她的练功服和芭蕾舞裙更是破旧不堪,发给她时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手了。她经常因繁重的练习而双脚流血,因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不停感染。回到家,全家都挤在一所逼仄的公寓里,没有自来水,她没办法及时清洗干净自己身上的脏污和汗水,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去楼下排队打一桶水再上楼。
她大部分同学也过得同样悲惨,有一次演出中,一个舞者的芭蕾舞裙被后台的煤油灯点燃,最终自己也被烧伤致死,还有许多同学死于结核病,若她们不能在歌剧院办会员的现生中找到“保护人”(金主),便要踏入娼妓的生涯。

德加作品中的小舞者
德加与其他在歌剧院办会员的老色鬼们不同,他厌女,传说可能由于他在青年时期曾在风月场感染过性病,那之后他对女性敬而远之,终身不婚,而所有跟他有过交集的人里,也几乎从没流传出关于他的艳闻轶事。他之所以选择玛丽,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吸引了他,真相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她平凡,小舞者既不迷人也不媚人,她身上穿着的不是华丽的演出服,而是一件朴素的练功服,她仰着头,并不看向那些看着她的人,没有散发出一点男性群体的魅力。德加在刻画她的时候甚至在她原本就朴实的面孔上做了一些丑化,让她更符合一些“贱民”的特质,就如同一位“偶像的破坏者”,蔑视那些关于舞者犹如女神附体的陈词滥调,而揭露出“由于机械单调的蹦跳动作而日渐麻木愚蠢的雇工”那一面。
当时的画家,经常不经过模特的同意而自行跟模特进行性行为,德加不是他们的一员,同样作为歌剧院的会员,他曾去找院长替一位舞者说情,请求给她加薪,也曾经替另一位舞者争取到想要演绎的角色。他看到的不是舞者们享受万众瞩目的一面,而是作为体力劳动者辛苦劳作的一面,他也想让看他画的人们看到真实,而不是去迎合资本家的审美。
玛丽给德加做模特的报酬是做芭蕾舞者报酬的四倍,还不用辛苦地练习,所以她很乐于这么做。然而由于频繁为德加做模特,玛丽因为合同期未满和缺勤过多而遭到解雇,甚至她需要为自己的缺勤进行赔偿,而她缺勤本就是为了赚钱。故事并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在她遭到解雇之后,德加并没有给予任何意义上的帮助。德加跟小舞者玛丽是再纯粹不过的合作关系,德加既没有少付玛丽一分钱也没有多给玛丽一分钱。
后来,小舞者玛丽的生命停止在四十三岁那年,离开德加之后能找到的关于她的资料甚少,她的姐姐离开歌剧院之后成了一个小偷,最终在贫困中生命定格在了三十七岁,她的妹妹则格外幸运,先是在芭蕾舞界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后来转行成为一名舞蹈老师。

献给所有被遗忘的卑微生命
作者卡米耶·洛朗斯说:“我很难给这本书收尾,因为我离不开玛丽。”这个来自十九世纪身形单薄的十四岁小舞者,不止萦绕在作者心头,也会令每一个读过她故事的读者不断回想。
就如同德加的雕塑风格一般,《十四岁的小舞者》这本书作者的文字也是真实到有些残忍,全书非虚构写作,通过探寻小舞者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浪漫文艺背后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光鲜大人物背后虚伪凉薄的一面。
这些曾经在历史上演的真实的一角,被德加通过小舞者的雕塑记录下来,而《十四岁的小舞者》这本书也通过德加的雕塑,将淹没在艺术史上卑微的小人物,进行了一次有血有肉的复活。

《十四岁的小舞者》
[法]卡米耶·洛朗斯
译者: 吴乐冰
当风起时,随风而舞
豆瓣丨大风文化
小红书丨大风文化Silent Rhapso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