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中的女性:被遮蔽的创造力
冯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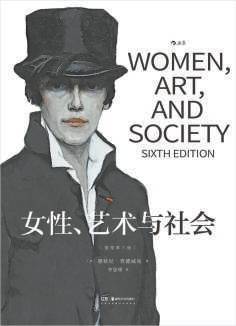
《女性、艺术与社会》 惠特尼·查德威克 著 李思璟 译 后浪·湖南美术出版社
艺术史中女性创造力的系统性遮蔽,在约翰·佐法尼1772年的群像画《皇家艺术研究院的院士们》中显露无遗:画中,杰出的男性艺术家们围绕着裸体男模热烈讨论,而两位女性创始院士——安吉莉卡·考夫曼与玛丽·莫泽,却仅以半身肖像的形式被悬置于墙面。她们从艺术的创造主体,被降格为被凝视的客体;墙上画像如同一个隐喻,直观地宣告了女性被排除在艺术创作核心圈之外的历史事实。
这一局面直至1971年才被打破。艺术史学者琳达·诺克林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史认知。她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天赋的缺失,而是社会制度与文化机制的系统性压制:女性被禁止进入艺术学院学习人体写生;她们的社会角色被限定为母亲与家庭照料者;整个艺术价值的评判体系,也深植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诺克林的发问,正式催生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在后续著作《女性、艺术与权力》中,她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史作为父权意识形态载体的本质,并以马奈《奥林匹亚》中模特维克托莉娜·默兰的凝视为例,剖析了男性艺术家如何将女性身体建构为被动的欲望客体。
诺克林开启的批判之路,在1990年被学者惠特尼·查德威克推向纵深。她的里程碑著作《女性、艺术与社会》(三十多年里历经五次修订),以宏大的历史视野,重构了自中世纪至今的女性艺术创作史。查德威克的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坚决突破“天才”神话,拒绝将个别成功的女性艺术家视为“超越性别的例外”,转而深入剖析社会如何系统性塑造艺术生产的条件。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虽获认可,却被制度性地限制于肖像画领域——只因女性被严禁研习更为“崇高”的宗教与历史题材。其二,犀利解构艺术史的话语霸权,揭示“装饰性”“感伤”等评价术语,实为维护“高雅艺术”男性中心特权的工具。其三,引入革命性的交叉性视角,在著作后续版本中,纳入对种族、阶级、性向等维度的关注。非裔艺术家费斯·林戈尔德的拼布艺术即为明证:她的作品既重述了被主流历史湮没的黑人女性经验,同时也批判了白人女权主义的内在局限性。
回望佐法尼的画作,墙上的半身像并非孤例,它是艺术机构系统性排斥女性的一个缩影。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在考夫曼与莫泽之后,近150年间再未接纳任何女性院士,其排斥机制深刻而多重:通过禁止女性接触人体写生,从根本上剥夺她们参与主流艺术创作的能力;将鲜活的女性创作者,转化为画框中供人凝视的胸像客体,从而消解其主体性与话语权;更因女性被隔绝于学院教学体系之外,导致艺术经验与技艺的代际传承链彻底断裂。
这种系统性的排斥,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女性抄本画家、北方文艺复兴的卡特琳娜·范·赫默森等众多案例中反复重演。即便是巴洛克大师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笔下那些充满力量与戏剧性的作品,也长期被错误地归属给其父奥拉齐奥——艺术史正是通过“归属误判”这一隐蔽手段,持续抹除女性的作者身份,直至20世纪,这些名字才得以重见天日。
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理论武器,亦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演进:20世纪70年代,聚焦于发掘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如诺克林策划的展览《1550-1950年的女艺术家》),但尚未质疑传统的“伟大”艺术标准;80年代,转向对父权制艺术话语的批判(如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对“女性特质”社会建构的分析),但相对忽视了种族与阶级的交叉维度;90年代后,进入强调交叉性的解构阶段(如哈莫尼·哈蒙德的酷儿艺术实践),但也面临着被学术体制吸纳而弱化批判锋芒的风险。这种理论的迭代,在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芭芭拉·克鲁格的宣言式作品《你的身体是战场》,将女性身体转化为政治场域,不仅挑战男性凝视,更通过视觉符号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机制,成为福柯话语理论与拉康精神分析在艺术场域的具体实践。
进入21世纪,《女性、艺术与社会》第六版新增了弗拉维娅·弗里杰里等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当代女性艺术的多维突破。辛迪·舍曼通过自拍摄影戏仿并解构各类文化符号,拒绝成为“被言说的客体”,夺回了身体与形象的叙事权。在全球视野下,中东艺术家莎拉·穆哈的作品,揭示了头巾之下个体的主体性与复杂经验,挑战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在技术革新领域,草间弥生的“无限镜屋”等沉浸式装置,创造了消弭性别界限、探索身份可能性的新场域。这些实践表明,女性艺术已超越早期的“正名”诉求,转而将艺术本身作为批判的武器,直指殖民遗产、生态危机等深层的全球权力结构,彰显出女性的创造力正成为重构人类共同叙事的核心力量。
《女性、艺术与社会》的终极价值,在于它将一部艺术史,转化为一份深刻的文化权力诊断书。查德威克将从中世纪抄本画家到数字时代艺术家的线索连缀成网,无可辩驳地证明:女性从未缺席艺术的创造,只是被主流叙事实施了“选择性失明”。书中那三百余幅图像,如同一幅幅星图,不仅照亮了艺术史缺失的半壁天空,更映射出所有边缘群体不屈的抗争之路。从佐法尼画框中被“封印”的胸像,到今日敢于定义自我价值的多元创作者,这段漫长的抗争历程揭示了一个真相:掌控叙事权力者,即掌握存在的定义权。(作者为书评人)
上一篇:主力资金 | 尾盘4股获大幅抢筹
下一篇:用油画讲述内蒙古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