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8木工柬埔寨务工遇险:3人“退货”,1人被转卖4次!
金边机场的阳光没那么刺眼,8位四川木工下了飞机,心里想的都是“干上几个月,挣个十几万,回家盖房娶媳妇”。
可他们没有想到,等在机场外的,不是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竟然是诈骗园区的“人贩子”。短短几天,高薪梦碎,命运急转直下:3人被暴力“退货”,1人被转卖4次,4人至今失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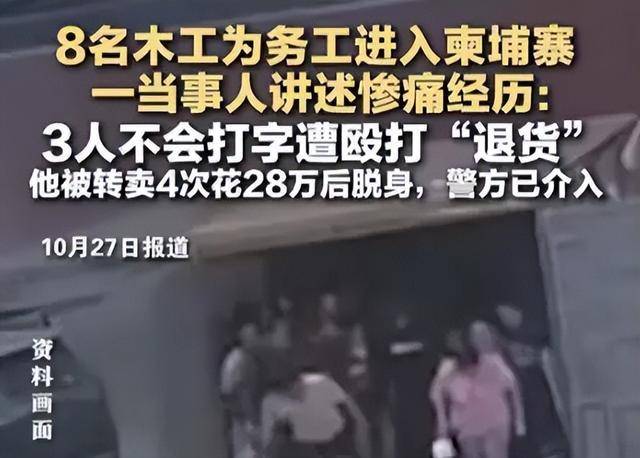
这活生生的现实,发生在2025年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更令人揪心的是,这样的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高薪梦是如何被包装成陷阱的?
所谓的“高薪出海”,听起来很美,尤其是对一群经验丰富的木工来说。他们不是头一回出国干活,有人去过老挝,有人手艺过硬,干活快、效率高。可正是因为经验,他们更容易陷入心理惯性:出国干几个月,挣得比国内一年还多。骗子正是抓住了这点。

这起事件中,诈骗链条的第一步就很老练——熟人介绍。一个叫王某俊的人,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招工消息:金边酒店装修,日薪高、包吃包住、正规合同。听起来就像是标准的海外用工项目。而关键人物余某,则是他们的“熟人”,也是这场骗局中的信任中介。他的出现,让这份工作看起来不再“陌生”,也降低了所有人的戒心。
更“专业”的,是骗子准备的那套文件——假的劳工批文、假的合同、甚至连“项目介绍书”都伪造得有模有样。从头到尾,看起来就像一个正经的施工项目。公安部反诈专家曾提到,技术工人因跨境电信诈骗受骗的比例,比普通务工者高了47%。这不是因为他们更“傻”,而是因为骗子更懂他们在找什么。

技术含量高、工资高、有熟人、项目正规,看似天衣无缝的组合,其实就是一个“定制型陷阱”。它不是乱撒网,是精准狙击。
当人被当成商品,价值只看“能不能赚钱”
被骗进西哈努克港的诈骗园区之后,所谓的“装修活”根本不存在。他们被带进一个封闭园区,手机和护照第一时间被收走,24小时有人持械看守,没人能随便说话。
这群木工被当成了“商品”——有没有用,就看你能不能在电脑前“打字”搞诈骗。3人因为“手太笨”,不会打字,被老板视频检查后直接打了一顿,然后被“退货”。人不值钱,就像瑕疵品,被暴力处理后赶出去。

而另一个受害者陆某的经历,更像是一场“地下拍卖会”。他为了脱身,主动提出赔偿13万元“补偿金”,结果被转卖了4次。每一次转卖,都像是在拍卖会上的加价,每一次谈判,都是筹码的博弈。他不是个体,而是被反复压榨的“资产”,价值被榨干了,才可能被“放行”。
这背后,是一整套冷冰冰的逻辑:谁能赚钱,谁就有“价值”;谁不能赚钱,就成了“废品”。园区不是在做诈骗,是在做“人力资源的股票交易”。

这些人进来之前是工人,出去的时候连人都算不上。他们的劳动、身份、甚至痛苦,都被量化、评估、交易。而维系这一切的,是彻底去人性化的暴力管理:电击棍、殴打、封口、恐吓。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让人听话,把人变成工具。
失联者的等待和跨境救援的难题
在四川的村庄里,4个家庭至今没有等来亲人的消息。他们收到过匿名电话,要求支付25万元赎金,才能“买人回来”。有人卖了房,有人借了高利贷,有人甚至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的。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赌一把。

陆某能逃出来,是因为他偷用了别人手机,幸运地联系上了救援组织。最终花了28万元才脱身,其中包括“谈判费”“疏通费”——这些词听起来像商业交易,实则是人命的价格标签。
而警方这边,四川多个地市已经立案,开始调查取证。但境外犯罪,执法权限有限,中国警方无法直接进入柬埔寨园区抓人,只能依赖国际合作,走联合调查程序。这就意味着,时间慢、效果差、过程复杂。而诈骗园区背后,往往还与当地某些势力勾结,形成保护伞,让打击行动步履维艰。

早在去年,《环球时报》就报道过中柬联合执法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确实有不少窝点被清除。但正如草原上的野火,烧了一片,又会从别处重新燃起。诈骗团伙换个园区、换个名字、换个“招聘简章”,又能卷土重来。
而在这场跨国博弈中,最无力的,是那些收到“你儿子被卖了”的电话,却没钱赎人、也不知道找谁的父母。他们拿着照片、翻着通讯记录,在派出所门口坐一天又一天,只盼一个消息。
这8个木工的故事,不是什么孤立事件。他们的遭遇,是“高薪出海”泡沫破灭的现实剪影。陆某说:“这辈子再也不敢出国务工了。”这句话不只属于他,更是一个警钟。

对于出国务工者来说,正规渠道不是“麻烦”,而是最后的底线。所有的“熟人介绍”“高薪招聘”,都应该用再多一遍的怀疑去验证。哪怕多跑几家中介、查几次文件,也比走错一步、深陷泥潭来得轻。
这一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跨境打击电信诈骗与人口贩运,早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它需要输入国、输出国共同发力,堵住漏洞,拆掉园区,断掉资金和人流链。国际社会如果继续放任这些黑园区“合法存在”,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
信息来源:8名四川籍男子赴柬埔寨“应聘木工”,结果进了诈骗园区,3人不会打字遭殴打“退货” ,有人被转卖4次…——上游新闻2025-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