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刘洪彪先生的超越论和冠军论引发巨大争议,很多民众包括部分书法家都纷纷站出来挞伐刘洪彪先生,认为他狂妄自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正成先生曾称当今书法是全面堕落的时代,这一言论则获得众多认同。

刘洪彪先生是在什么原因下提出了他著名的两论,很多人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们依旧选择忽视真相,将论点的初衷归咎于刘洪彪先生的张狂,这让刘洪彪先生因此蒙冤难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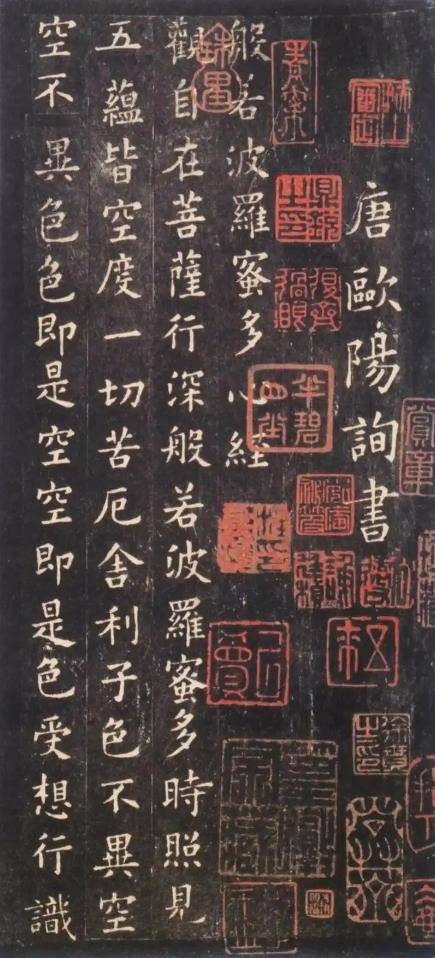
民众对待书法的普遍态度就是“今不如古,内不如外,生不如死“,盲目的尊古贬今、崇洋媚外是源于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

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当代书法自然处于日渐消退的趋势,并且不仅仅是书法,还有社会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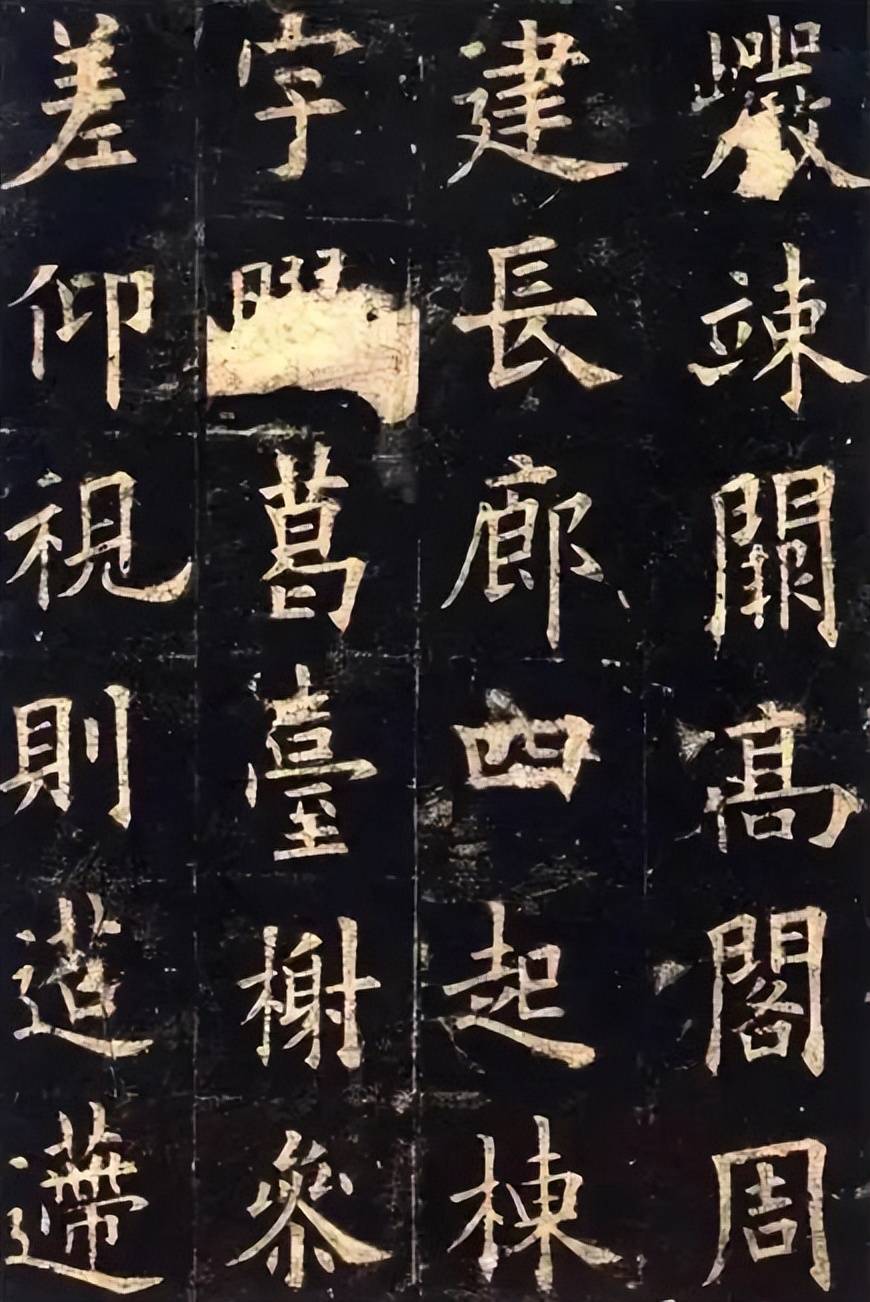
更有人将贬低今人成就来标榜自己赋予见识,背离专业评价,完全沦为情绪宣泄。书法已经进入纯艺术的发展阶段,再用实用性的标准去审美衡量已经不再合适。

但是就是有人无视文化变迁实际,强行对标,主要目的不在于书法艺术本身,而在于对当今书坛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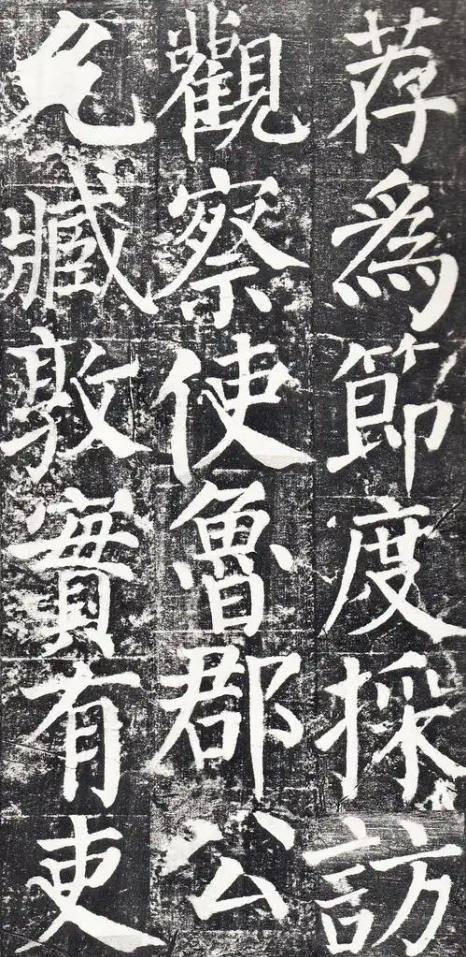
书法成为发泄这种不满的便捷渠道,因为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象征地位。批评者表面上讨论书法,实则表达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失落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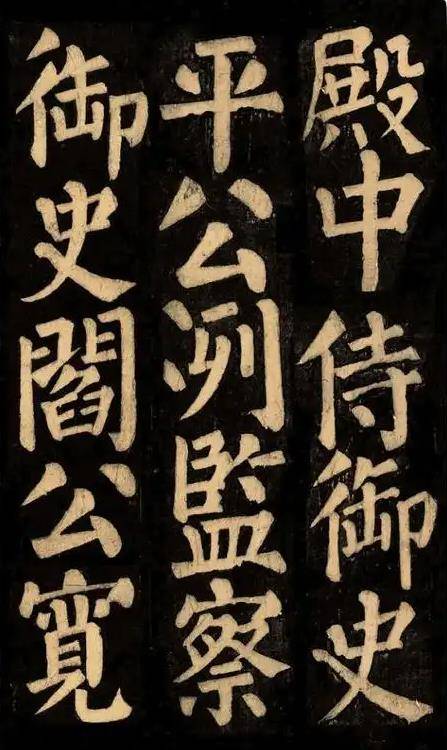
这种将复杂文化问题简化为“今不如古”的二元对立思维,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文化领域的对立。

书法作为一门有着严格规范的艺术,需要基于专业知识的评价。然而,当下许多批评完全脱离书法本体的讨论,沦为纯粹的情绪表达。

笔墨、结体、章法等专业要素被忽视,代之以空洞的价值判断。这种去专业化的批评风气,不仅存在于书法领域,也弥漫在整个文化评价体系中。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重建书法评价的专业性和历史感。首先,应当将书法作品放回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理解,避免跨时代简单比较。

其次,需要尊重书法从实用向纯艺术转变的事实,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再次,应当摒弃“尊古贬今”的思维定式,以开放心态看待当代书法的探索与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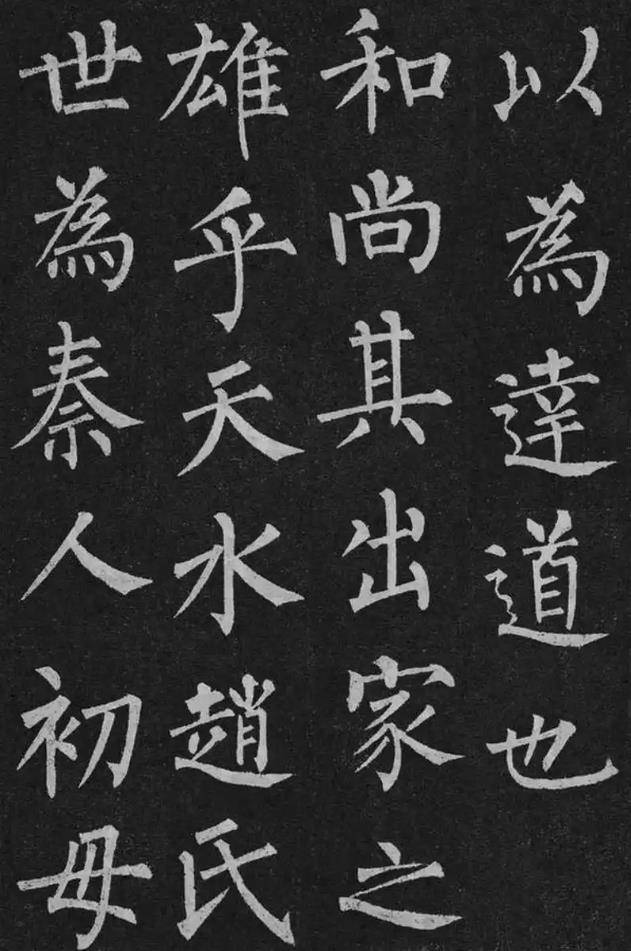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书法讨论应当回归艺术本身,关注笔墨语言的表现力,而非沦为文化立场的象征性表达。

刘洪彪先生的“蒙冤”,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时代理性沉沦的缩影。当情绪压过理性,当站队取代思考,真相便成为第一受害者。

书法的未来不在于对古代的盲目崇拜,也不在于对现代的轻率否定,而在于基于专业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唯有跳出“今不如古”的思维窠臼,书法艺术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

在这场喧嚣的论争中,我们或许应当重温孔子的智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待书法传统,既需要认真学习,也需要独立思考。

盲目崇古与轻率贬古都是不可取的极端。书法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的平衡,而这平衡需要理性而非情绪,需要专业而非偏见,需要开放而非封闭。

当键盘声渐息,当情绪平复,或许我们能重新聆听那些被喧嚣淹没的声音——包括刘洪彪先生未被真正理解的初衷,也包括书法艺术本身沉默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