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绳系日 丨 韩天衡篆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上)
为致敬海派艺术大家韩天衡先生八十载孜孜矻矻的艺术求索,全面呈现其融古铸今的卓越成就,“长绳系日——韩天衡学艺80年回顾展”正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展出中。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刊载学者文章,带大家更深入地了解韩天衡先生的艺术成就。
韩天衡篆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上)
沈慧兴
一枚印章,竟蕴含着哲学、文学、美学、文字学、历史学、材料学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元素,这是笔者拜读了韩天衡老师(以下简称韩老师)《长绳系日--韩天衡学艺八十年回顾展作品集》的篆刻作品后,得到的一个直观感受。同时通过对韩老师书法、绘画、文房等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进一步领悟到韩老师篆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是一个多么生动鲜活、内涵丰满而又漫长艰辛的探索过程。
桐乡丰子恺先生曾说:“金石篆刻是中国艺术宝塔上的一颗明珠”。三千多年来,篆刻艺术就像一根细长的红线,在历史的长河中细如发丝,却从未中断,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顽强的生命力,令古今无数印人为之着迷,为之兴叹。韩老师对篆刻八十年的痴迷与热爱,实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在中国艺术的宝塔上熠熠生辉。
笔者以韩老师八十年篆刻艺术的阶段性作品为素材,结合本人篆刻创作的体会,从历史与宏观的角度,梳理提炼出韩老师篆刻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艺术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并进一步提出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的启示意义。希望通过此文,对韩老师篆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所总结,对热爱篆刻艺术的当代印人有所启发。

“长绳系日——韩天衡学艺80年回顾展”现场
一、知白守黑、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用简明的语言体现出深刻的道理,用于完善自己的精神修养和帮助他人完善思想的学科。在西方哲学中,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知白守黑、自然和谐的哲学观,是艺术创作遵循的基本原理。孔子《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古代中国为人处世的哲学观,也是艺术创作的辩证法。韩老师在数十年的篆刻艺术创作中,自觉应用辩证的艺术创作思维,结合中国道家阴阳互补、相互生发的理论,实现了篆刻艺术计白当黑、辩证统一、道法自然的艺术哲学观。
“计白当黑”的哲学思想,在章法布局中的大胆应用,是韩老师篆刻最显著、最核心的哲学观念之一。他深谙中国道家“有无相生”的原理,在印章布局中,不仅精心经营着文字的位置,更自觉地运用和经营留空与留红。他敢于大胆留白,甚至让大面积的空白成为印面的主角,这是一般印人难以想像的胆识。这些“虚”的空间并非空洞无物的存在,而是具有充满张力、呼吸感和想象空间的存在。“空白”与“实线”的相互依存、相互生发,如同道家的黑白双鱼“八卦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盛而白衰,黑衰而白起,阴阳互补、浑然一体,是对篆刻艺术“计白当黑”的最好诠释。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章法处理上就出现了大片留红的作品,如1981年创作的“是有留人处”白文印,将“人”字内部及底下留出了大片红地,与其他文字的“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同时文字线条的走向、疏密、聚散,都与留白形成呼应,营造出“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节奏感和空间感。这是对邓石如、赵之谦篆刻章法的继承发展,更是对“虚白”的极致重视和运用,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以无胜有”的辩证智慧。在2000年创作的“喜出望外”白文印、2009年的“味外心绪”白文印等作品中,这一章法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成熟。而在“多岐亡羊”“般若”“妙吉祥”等朱文印作品,印内空间的留白已经达到他人不敢尝试的地步。这些大块的留红与留白,是韩老师“艺高人大胆”的有力证明,也是他在“计白当黑”艺术哲学观的引领下,在篆刻艺术方面的大胆实践和自觉追求。今年创作的篆刻作品“空”,更是将这一创作理念作了探索性尝试,开拓了“会意印式”的篆刻新境界。或许数年后,这一作品会像赵之谦的“丁文蔚”白文印一样,开创齐白石单刀直入的新印风,成为一种全新的篆刻艺术表现形式。韩老师章法布局追求“看似不经意”的意趣,往往是在几十个设计稿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结果,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偶然之作。如海上之冰山,看到的只是海面的一角,而大量的体积,都隐藏在海面之下的。恩师孙慰祖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以前韩老师要求我们多学哲学,目前来看真的非常有用。”

韩天衡先生作品 喜出望外(2000年)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自然和谐地应用于韩老师的印面文字中。在韩老师的篆刻作品中,充满了方与圆、直与曲、刚与柔、粗与细、工与写、聚与散、动与静、古与今等强烈的对比和矛盾,但这些矛盾,最后都能和谐地统一在印面之中,这是韩老师自觉应用辩证思维进行艺术创作的又一个鲜明特点。调和印内文字矛盾,绝非易事,需要将这些对立元素进行巧妙调和,使之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才能创作一方成功的篆刻作品。韩老师的篆刻作品,面目甚多,除了纯正的秦汉白文、朱文外,汉玉印、吴让之式的朱文印等风格都有所见,而韩老师的鸟虫篆作品,则是他篆刻风格中最突出鲜明的面貌。每一种风格,都能保持一定的基本的面貌,这也是韩老师篆刻高出时辈的主要方面。所谓肉有肉味、菜有菜味,一方印的基本风味,是严格地把握住的。在他的篆刻作品中,既有味厚酱浓、皮酥肉烂的红烧肉(汉粗白文),又有配色鲜明、吊人胃口的什锦菜(多种形象的鸟虫印);既有棱角分明、线如屈铁的白切肉(汉玉印),又有线条柔劲、色味俱佳的清汤面(圆朱文印)。韩老师的篆刻创作,是既能做好一道菜,也能做出一桌菜,这是韩老师辩证地应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成功地运用辩证法则,创造出不同的篆刻面貌而能和谐统一的高明之举。如韩老师2001年创作的“秦始皇”白文印,线条基本是粗壮的白文,而结构上又加了一个秦印的丁字界格,这样就实现了线条丰满而秦印风格显著的创作目标,让人过目难忘。在韩老师的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一个印面中既有刚劲挺拔的直线,又有婉转流畅的弧线;工整的布局中既有流畅的线条,又会出现不经意的崩裂;既有严谨规范的小篆,也有韩老师自家面貌的篆书构成。在韩老师2009年创作的“诗心文胆”朱文印、2012年的“不知有汉”朱文印、2016年的“且饮墨沈一升”朱文印、2019年的“言之不预”朱文印中,明显地感受到韩老师篆书与印风的高度统一,这种书法与篆刻风格的统一,是每一位篆刻家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这种在矛盾中求统一、在对立中求和谐的篆刻创作手法,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哲学思想的完美诠释。韩老师在《豆庐印屑》一文中说:“刻印之决窍为三个字‘辩证法’。将众多矛盾放进印面,令其吵,令其闹,令其纠缠纷争,最终复归大团结、大拥抱,才是本事。”印面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平衡与稳定,而实现这个艺术理想的前提就是印面文字的统一。试想如果印面文字的每一根线条风格都机械雷同,那是多么的索然无味。君子和而不同,一个印面,就是一个组织,一个家庭,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最终能和谐地集中在一起,这便是篆刻艺术的魅力所在,我想韩老师也是深有同感的。

韩天衡先生作品秦始皇(2001年)
韩老师不仅有统一印面文字风格的创作力,同时也具有“举一反三”“化身千百”的创变力。即使在鸟虫篆这样一个极小的天地内,韩老师也能创作不同风格的鸟虫篆作品。如“百乐斋”的沉着厚重、“与时俱进”的剑饰篆意、“行者常至”的丰茂流美、“上善若水”的飞动劲健、“兴之所至”的深沉古拙、“吉祥如意”的屈铁铮铮、“一日千里”的多姿多彩,都呈现了千百化身、出乎想象的艺术风貌。而更令人折服的是韩老师以“如意”两字,在2009-2023年间,创作了九方不同风格、不同章法的篆刻作品,其出神入化的变化创新能力,是如来佛的万千化身,是一个艺术家实现创作自由的显著标志。韩老师刻的肖形印,造型也极有个性,十二生肖的变化,往往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今人,显示出韩老师独特鲜明的样式。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09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1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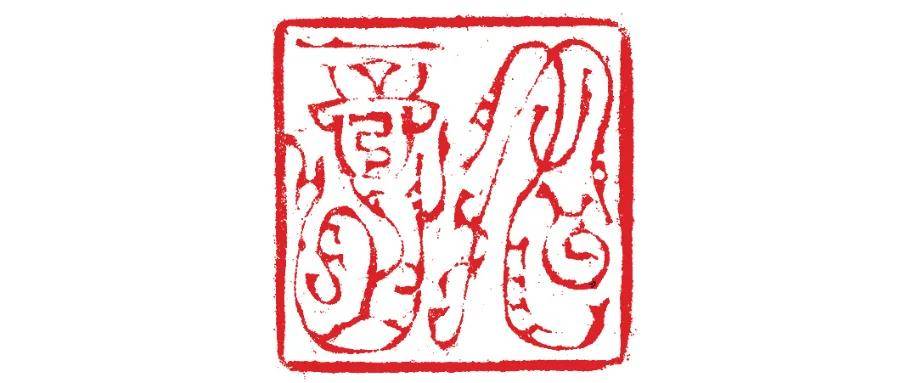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7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7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9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19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20年)

韩天衡先生作品 如意(2023年)
“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是篆刻艺术的终极追求。韩老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篆刻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要真正理解它,就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艺术的复杂联系中作全面的考察。韩天衡强调篆刻应追求自然天趣,反对过分雕琢和匠气。如他1975年创作的“壮暮”“落墨”“苦篁”三方竹根印,就是利用了竹根天然的外形,再配以古拙的朱文线条,呈现出浓厚的文人气息。韩老师同时也是藏印赏石的名家,各种印石一眼便识。作为一名篆刻家,他也熟悉每一种印材的特点与优劣,如何尊重与利用印材本身的特性,选择与之匹配的艺术风格,也是韩老师经常思考的内容。他常利用石质的天然崩裂或瑕疵,巧妙地化“弊”为“利”,使其成为艺术表现的一部分。如用一枚四面博古浅雕的古兽钮和田玉,刻了一方“豆庐”鸟虫篆印,达到了形式内容的完美统一。一方“三省堂”的陶朱文印,将边款文字写在四周及顶上,与古陶器的创作形式相吻合,也是因材施法、活学活用的一个印例。总之,什么样的印石最适合哪种风格的作品,在韩老师的思维中是十分清晰的,这样综合全面的修养,也是一般篆刻家达不到的。韩老师在追求篆刻线条“金石味”的把握上,也有独到的审美能力,他强调刀与石碰撞产生的自然效果,不过度修饰光洁。他对线条的老嫩生熟程度,火候把握十分恰当。如同炒青菜,太生不能食,太熟口感差。这种对自然之“道”的尊崇,追求创作内容、创作材料与艺术思想三者的和谐统一,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篆刻艺术实践中的生动体现。韩天衡晚年的篆刻艺术风格,尤其是“草篆”入印和写意、浑朴的作品,实现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实现“返璞归真”、“由熟而生”的美学追求,在看似粗服乱头、稚拙率意的表象下,蕴含着深厚的功力和精妙的构思。线条更加概括、简练,甚至带有“生涩”感,这种人印俱老的“拙”,是经过高度提炼的“大巧”,是洗尽铅华后的真醇,是艺术成熟的标志,深刻契合了老子“大巧若拙”、“大象无形”的哲学理念,体现了对艺术本质和生命本真的终极追求。
韩天衡先生作品 三省堂朱文印写款
韩老师篆刻艺术的哲学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在西方古典哲学和辩证法的基础上,以道家“虚实相生”、“道法自然”为核心,又融合儒家“和而不同”、“技进乎道”的进取精神,并在古与今、人与天、工与写、巧与拙等一系列辩证关系中,展现出深邃的思辨性和高度的统一性。 他的篆刻艺术,不仅是文字与刀石的结合,更是一个浓缩的哲学宇宙,体现了艺术家对生命、自然、历史的深刻体悟和独特表达。韩老师的篆刻作品,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的精神载体。
二、根植传统、守正创新的历史观
韩老师的篆刻艺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是在长期的创新变化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他的篆刻艺术,不仅表现出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印学观念的鲜明特色,同时也具有西方文化艺术的现代构成与视觉冲击力。一枚印稿,融合了印学、文字学、美学、材料学等诸多学科的丰富知识和呈现方式。他对印学史的深入研究,是以1980年著《中国篆刻艺术》、1985年编《历代印学论文选》、1987年编《中国印学年表》、2003年编《中国篆刻大辞典》、2011年编《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等历史性的经典著作为基础的,充分彰显了韩老师深厚全面的印学理论修养。同时他还编纂出版了《秦汉鸟虫篆印选》《味闲草堂古印存》《古玉印精萃》《古瓦当文编》《古玉印集成》等专门的印谱,为篆刻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韩老师还编纂了《天衡印话》《韩天衡谈艺录》《篆刻病印评改200例》《改“瑕”归正--韩天衡评印改印》《简明篆刻教程》等篆刻技法创作类的著作,以及大量的个人书画篆刻作品集。韩老师艺术理论的全面性,除了书画印风格的鲜明特点和高度统一外,他还对印章、砚台、笔墨、纸张等文房类知识的研究也情有独钟,出版有《文玩赏读》《砚印赏读》《砚韵墨香》《兰室长物—历代文房艺术》《文砚在甬—历代铭文砚展》《兰室撷珍—历代文房艺品》《藏杂杂说—我与收藏的故事》等大批收藏鉴赏类的著作。截止今年4月,韩老师已编纂出版各类著作158种,著作等身,令人惊叹,树立了一个传统而又现代的艺术家的崇高形象。

韩天衡著作书影

韩天衡著作书影
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批判性继承。韩老师具有宏阔的篆刻史视野,他对战国秦汉以来的篆刻艺术史,特别是明清流派印直至近现代诸家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不仅熟练掌握了秦汉印的创作技法,更理解明清各家各派产生的历史背景、艺术主张和局限得失。韩老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坐标和时代优势,既有对传统的敬畏,又有开创篆刻艺术新局面的使命感。他提出了“传统万岁,创新是万岁加一岁”的著名艺术论断,是基于对篆刻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继承,才赋予了他篆刻创新的底气和力量。早在1988年8月,韩老师在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大会学术交流会上,发表了《论印五题—对当今兴旺印坛的几点思考》一文,就对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出新有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他说:“辩证法告我们:历劫不磨的优秀传统是往日之新,今日公认的新面,势必成为明日的传统。轻率粗暴地蔑视传统,正是出其意料地把想往的创新也纳入蔑视、砸烂的范围。”韩老师对篆刻艺术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是基于正确的历史发展观,并一直遵循着这个观点。韩老师的篆刻艺术,是在对中国篆刻史深入了解、烂熟于心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他的艺术语言和线条构成,如果99%是传统的影响,而1%就是韩老师的可贵创新。而那些稍有继承,就大谈创新的艺术家,相对于韩老师的深厚学养,往往就相形见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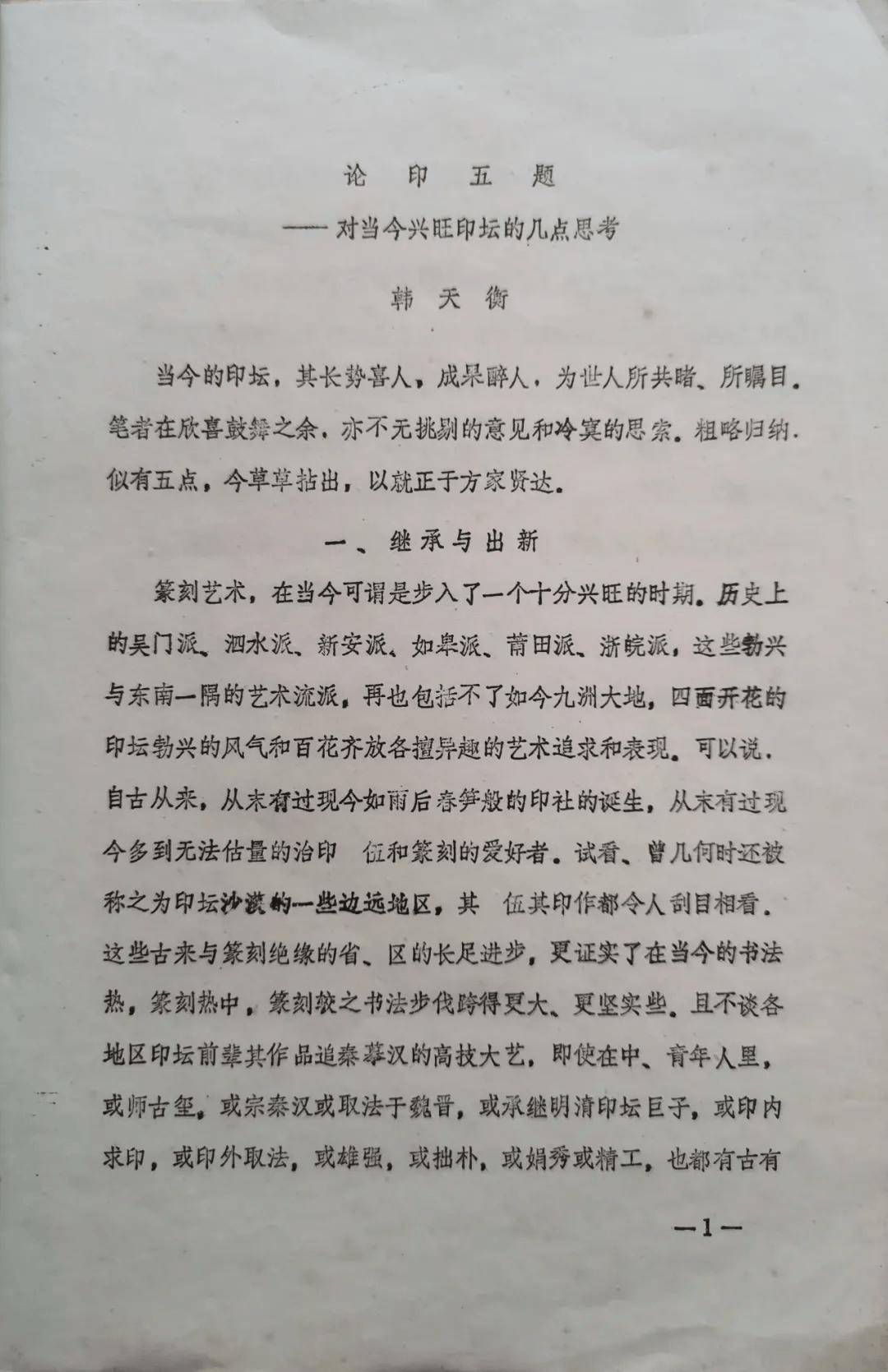
韩天衡《论印五题》论文首页
同时韩老师对中国印章艺术的历史遗产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批判、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他善于从历代名家大师的篆刻作品中汲取养分,又能敏锐地发现其艺术短板或时代局限,从而明确自己突破的方向。他今年8月29日在韩天衡美术馆举办的“长绳系日--韩天衡学艺八十年回顾展”讲话中表示:“艺术创作不要与古人雷同,不与当代人相同,还要与昨天的自己不相同”。这个“三不同”的艺术创作观,是韩老师对《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深刻理解,也是在深入了解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在众多的历史和当代篆刻名家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这一追求艺术个性的观点,也是与吴昌硕提出的“艺无双”理念不谋而合的。事实证明,吴昌硕只有一个,齐白石也只有一个,而那些依附于某家某派的印人,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陪客。
强烈的创新观念和时代意识。韩老师认为艺术贵在创新,“新”是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对秦汉玺印、明清流派印有精深研究和继承,但绝非食古不化,而是强调在深刻理解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强烈的个人性情、时代气息和艺术创造力。他反对陈陈相因的旧调,强调艺术家必须要有自己的面貌。创新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是他的核心创作理念。篆刻作品表现出奇崛、雄浑、灵动、现代的印风,其构成、线条、章法都能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但又被赋予了全新的形式和强烈的时代感。如韩老师2005年刻的“大道必简”白文印,就是吸收了近代出土的汉简文字特点,形成了以汉简文字入印的先例,影响了当代孙慰祖、张炜羽等印人的创作风格。韩老师的创新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更是艺术思想和审美内涵的更新,反映的是当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他的印作既有深厚的金石古意,又具有现代审美的节奏感和鲜明的现代感。这种既古又新的风格,以“郁文山馆”朱文印、“意与古会”朱文印、“老大努力”朱文印、“豆叟草篆”白文印为代表,既看到了吴昌硕、邓石如、吴让之的影子,又鲜明地突出了韩老师草篆书的艺术风格。他以“食古而化”超强能力,将传统艺术元素吃进、消化,又创造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个人锋芒的艺术语言,体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辩证发展观,以及艺术家在传统与创新中确立的哲学思考。韩老师认为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篆刻艺术也是作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存在。这种发展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上升变化过程。历史上的名家作品,有历史的高度,但也有局限性,很多人往往在高峰面前望而却步。而韩老师深愔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根植传统、守正创新,以从容自信、坚定有力的步伐,用八十年的漫长岁月,登上了一个篆刻艺术的历史新高峰。

韩天衡先生作品 大道必简(2005年)

作者简介

沈慧兴,男,浙江桐乡人,1970年3月生于苏州。字泠君,室桐荫山馆,号泠道人。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先后师承西泠袁道厚、余正和孙慰祖先生。 1985年以来,作品多次入展西泠印社、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同时发表于《书法报》《美术报》《中国书法》《西泠艺丛》等刊物。篆刻作品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日本邮便发行纪念邮票十枚,并在日本馆举行首发仪式。2014年参加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中外嘉宾现场创作篆刻艺术作品。
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研究员、浙派篆刻艺术研究院研院务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嘉兴画院画师、青桐印社名誉社长等。
- 版权声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