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镇,找到自己的“南浔” 去南浔古镇景区 去古镇南浔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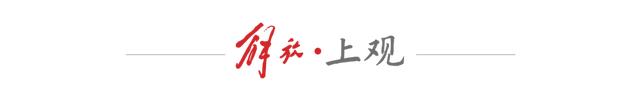
去南浔古镇,是很多年前就生出的心思。但是一直懒,想等一个特别机缘。前些天需要确定一个采风的地点,我脱口而出,去南浔吧。
想去南浔古镇,起因并不是古镇,而仅仅是它的名字,第一次听到,就让我联想到了“南柯”。有个南柯太守的故事,说淳于棼在醉梦中来到大槐安国,娶了公主,做了太守,百姓拥戴,权倾朝野,儿女绕膝,生活美满,却在遭到疑忌后,被遣还乡,一切成空。大梦醒来,残酒还在,他发现大槐安国原来不过是槐树下的蚁穴,一切繁华不过是一场梦中的泡影。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南柯太守传》,后人据此概括为“南柯一梦”的成语。
我当然知道南浔不是南柯,可走过进入镇子的长桥,然后沿着古頔塘故道的水岸漫步而行时,两岸的码头、石栏、民居,依旧笼罩着让我想要探寻的神秘,我甚至觉得,虽然是第一次踏足,但我是故人重逢,而不是初来乍到。拐进主街后没走几步,便是一座小石桥,小而古朴,像轻叹一样,几不可闻却让人心生波澜。桥的两端,连接着现实和梦幻,桥下漫透的河水,又曾流淌过多少浪漫和遗憾?四周的游人来来往往,还有人穿着汉服飘然而过,我突然忘了我,这哪里还有我,走在这里的,分明是大槐安国里的淳于棼。
我心里鼓鼓胀胀的,东张西望,想要跟人分享交流讨论倾诉,但同行的人明显没有我这样激动的情绪,看着时间差不多,领头的人张罗起午餐来。主街入口处就是一家餐馆,起了个“李白×××”的名号,但要等位;走到里街,又一个“××酒家”,打的是本地菜肴的牌子,食客稀少。当然选后者,清净、方便、有特色,正契合我们此行的主题。可惜菜单上没找到有别于其他古镇的特色菜名,接着端出来的菜品也真“方便”,四个人的六菜一汤,都是用一次性餐具盛放,软趴趴地被端出来,汤汤水水在老板手里晃荡,直让人肚肠都吊起来,满心都只有对老板的担心了。
接下来的体验也是起起伏伏。在游客中心问询的时候,看到柜台上有公示说,凭当日高铁票可以换门票,自驾的则没有优惠,我心里一失;准备掏钱的时候被告知景区不收门票,如果不进几个收费景点,只在街上逛逛就可以直接进镇,我又一惊。等用餐结束,遇到个小园子准备购票的时候,看到门口挂的铜牌上有联票的购买二维码,我瞬间一喜;同行的人指着牌子让我算,联票仅仅比几个景点门票的总价便宜5元,我只剩一哂。如今回想起来,心头又是一疑:这其实是策略吧?把各个景点的门票单价和联票总价都公布在一块儿,但凡上过小学的人都能算出来,联票并不合算,不如走到哪里买哪里,10元、20元的单票,显然是并不昂贵的自由。有这样的对比来烘托,大家掏钱时会更爽气吧?
当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20元、一个25元,总计45元的自由。定好行程就往前走。古镇的导览图做得极好,用写实加写意的笔法,画面清新雅致。頔塘及其支流是接近雨过天青的淡蓝色,两岸鳞次栉比的房屋粉墙黛瓦,掩映在深深浅浅的绿草绿树中。关键是房屋都沿河而建,河道相交,大约呈一个“厂”字形,房屋的聚落也就呈现为“厂”字形,四周及腹地则都是被树墙隔开的大片田野,用水彩画的色调、儿童画的笔法,把古镇塑造成“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情调。不知道是真的只有大片田野,还是被处理后的布局,总之你看着导览图,看到的是民居逐水而建,屋前有水,屋后有田,观图人如在桃源。
我就在桃源里由东而西,小景点略过,重点看的第一站是张静江故居。那副对联我早已耳熟:“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没读过什么书的小时候,知道的对联就两副,一副是蒲松龄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另一副就是这个。我是在知道南浔的时候,知道这副对联在这里的,因此这副联是“南柯”之外,我的“南浔印象”的第二层滤镜。在楹柱前久立不去,想起用响水方言告诉我这副对联的语文老师,想起尘土飞扬的教室和青春,想起曾被这副对联纠正和鼓励的向往,尊德堂中泛黄的光影便笼罩了全身。
往第二站去的路上,偶遇了通津桥。通津桥是座拱桥,苏州城里有座乌鹊桥,曾经也是座拱桥,桥身高耸,明代高启有《乌鹊桥》诗,说“乌鹊南飞月自明,恨通银汉水盈盈;夜来桥上吴娃过,只道天边织女行”。但而今的乌鹊桥是平的,与城市道路融为一体,完全找不到“天边织女”的影子。而眼前这座高耸的通津桥完全可以用来帮助你理解高启想要描述的诗意。大约因为桥下頔塘故道曾是水运要道,需要过大船的缘故,拱桥修得有高耸入云之势。看惯了江南常见的小桥流水,再站在这座桥上看两岸之景,或站在桥下看桥上之人,皆有“向云端”的赞叹。
下午三点,日光西斜,在两条河道斜十字形交汇处的咖啡馆里坐下。窗外沿河的卡座人头攒动,歇脚的、自拍的、看风景的,人人都沉浸而松弛。虽然我也很想坐到室外,但我由衷地愿意他们能坐得更久些,在下午的阳光和河水的荡漾中,做自由逸动的风。
所以虽然没有特色菜品,没有换到免费门票,我仍然愿意二刷南浔,也愿意向朋友推荐。其中固然有我个人加诸的滤镜,但我能有“南柯”和对联,别人就没有自己的心心念念吗?譬如“藏书楼”,譬如“小莲庄”,这些名字也许就让某个人无端联想到“扫地僧”,回忆起读书时对“莲叶何田田”的幻想。他们来,看到的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古镇,还有他们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沉睡于心底的梦。
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外地朋友宣讲苏州园林,告诉他们每个园林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只看假山、池水、花草、建筑,那的确各个园子看起来大同小异;但园林是园主人的生活之所,看园林,得要看每个园子的人文意蕴,看园名、楹联、题额,看园主人在其中寄托的心志情思,他的高标人格、理想追寻,譬如网师园的萱草,狮子林的禅机,沧浪亭的萧索——也就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每个园林的故事、每个古镇的故事。在人的参与下,每个地方自有风范;而走在古镇中,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南浔”。
原标题:《去古镇,找到自己的“南浔”》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余嘉
